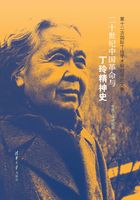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三
作为一个“左联”领导和“左联”机关刊物主编,丁玲对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的助推和对以“工农兵作家”为重心的“青年群众作家”的培养等,从实践层面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左翼作家,丁玲还躬身于创作实践。她根据“左联”大众化的要求,努力“尝试”,创作出了一批“大众化”的作品。她自陈,“在那个时期,秋白同志的文章(指《学阀万岁!》《大众文艺的问题》等鼓吹大众化的文章——引者),我大半都读过。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曾努力去创作,努力从各方面去尝试” 。于此可见,丁玲此期创作是在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联”大众化理论的影响下进行的。她也从以下三个方面忠实践行了“左联”“大众化”的原则:
。于此可见,丁玲此期创作是在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联”大众化理论的影响下进行的。她也从以下三个方面忠实践行了“左联”“大众化”的原则:
首先,是“用大众做主人”。“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美]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18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B00D2/15367253104216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7778558-mwqs99iPyEZtVJGlxhtG4Mz2ITfQJ3KL-0-385d2a9b09c1acb440008a97b0687af2) ,其早期创作大多以那时她相对熟稔的生活为题材,以自己相对熟习的现代知识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甚至其中有多篇还闪现着同时期作者自己的影子。用沈从文的话说,就是由于她“以个人感情为出发点”,所以,其“写作中心,是不能把它从本身爱憎哀乐拉开,移植到广大群众方面去的”
,其早期创作大多以那时她相对熟稔的生活为题材,以自己相对熟习的现代知识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甚至其中有多篇还闪现着同时期作者自己的影子。用沈从文的话说,就是由于她“以个人感情为出发点”,所以,其“写作中心,是不能把它从本身爱憎哀乐拉开,移植到广大群众方面去的” 。但是,到这一时期,她却自觉“把我的作风,从个人自负似的写法和集中于个人,改变为描写社会背景”
。但是,到这一时期,她却自觉“把我的作风,从个人自负似的写法和集中于个人,改变为描写社会背景”![丁玲语,见 [美]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26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B00D2/153672531042165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7778558-mwqs99iPyEZtVJGlxhtG4Mz2ITfQJ3KL-0-385d2a9b09c1acb440008a97b0687af2) ,从而使她的创作在题材和人物方面发生了“移植到广大群众方面去”的根本性变化。为了积累有关“广大群众方面”的人物和题材,如前所述,她还有意识地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生活”;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她还参加了闸北前线慰劳伤兵活动,因此,对官兵的生活也有了一些了解。
,从而使她的创作在题材和人物方面发生了“移植到广大群众方面去”的根本性变化。为了积累有关“广大群众方面”的人物和题材,如前所述,她还有意识地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生活”;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她还参加了闸北前线慰劳伤兵活动,因此,对官兵的生活也有了一些了解。
凭着这种有意识的收集和过去无意识的积累(如有关故乡农村的童年记忆),丁玲此期创作开始聚焦工农兵生活,因而,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几乎全都由“大众”来充任。他们中有农民(《田家冲》《水》《奔》)、工人(《法网》《消息》《夜会》)、革命者(《某夜》)、女佣(《杨妈的日记》)、普通市民(《多事之秋》)、下层官兵(《无题》)等。与早期创作相比,丁玲此期创作在题材和描写对象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谓是颠覆性的。在这一变化中,透露出来的是作者意识倾向的变化。“左联”“1931年决议”在强调“文学的大众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之后,还从五个方面对“写什么”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出“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 “广大群众的数重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等,是“大众的,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不难看出,丁玲此期创作在题材和描写对象上这些变化的发生,是丁玲有意识地贯彻“左联”题材原则的结果。
其次,是“替大众说话”。丁玲积极提倡“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并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其意就在使文学“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丁玲:《代邮》,《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也就是说,丁玲提倡写大众、 “用大众做主人”,其目的就在“替大众说话”,具体说来,就是要挖掘和彰显蕴藏于大众之中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从而进一步鼓动大众起来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以实现“推进社会”之目的。这样,丁玲此类小说既在“写什么”问题上选择“用大众做主人”,也就同时必然包蕴了“替大众说话”之主题。
《田家冲》和《水》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 的开始。其中,前者描写的是农村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者三小姐在农民中的宣传组织作用。后者以当年发生的十六省大水灾为题材,描写了农民先与水灾、后与官府作殊死搏斗的情景。1933年3月所作的另一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奔》,则以一群农民从离乡到回乡的过程为线索,展现了城乡无处不在的阶级对立和农民在工人的启发下阶级意识的觉醒。《法网》《消息》《夜会》等都市题材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工人的失业和痛苦生活,另一方面还表现了工人的觉醒和爱国热情。《多事之秋》《无题》等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民的抗议活动和“一二八”上海战事的描写,讴歌了普通市民和士兵的爱国热情,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揭露了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冯雪峰认为《水》“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了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
的开始。其中,前者描写的是农村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者三小姐在农民中的宣传组织作用。后者以当年发生的十六省大水灾为题材,描写了农民先与水灾、后与官府作殊死搏斗的情景。1933年3月所作的另一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奔》,则以一群农民从离乡到回乡的过程为线索,展现了城乡无处不在的阶级对立和农民在工人的启发下阶级意识的觉醒。《法网》《消息》《夜会》等都市题材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工人的失业和痛苦生活,另一方面还表现了工人的觉醒和爱国热情。《多事之秋》《无题》等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民的抗议活动和“一二八”上海战事的描写,讴歌了普通市民和士兵的爱国热情,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揭露了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冯雪峰认为《水》“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了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 ,这用来评价“替大众说话”的上述其他作品也是很为贴切的。
,这用来评价“替大众说话”的上述其他作品也是很为贴切的。
再次,是形式上浅切易懂。与题材、人物、主题等内容层面的追求相关,丁玲此期创作在形式层面上也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大体而言,这主要突出地表现在其描写手法和句式句法方面。丁玲早期创作是以绵密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曲折复杂的句式句法为其主要文体特征的。毫无疑问,能够接受和欣赏这类作品的受众,其主体应该是都市知识阶层。而到这一时期,丁玲所设定的受众群体却发生了从都市知识阶层到“大众”的巨大变化。因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够为这一新的群体所接受并进而发挥其社会作用,就成了摆在丁玲面前必须正视的问题。虽然“左联”提出了“必须简明易解”的文体原则(见“1931年决议”),但是,要把这一原则落到实处,自然还必须以对大众审美习惯的充分了解为前提。为此,丁玲作过一些调研工作。因为“大世界”是“群众娱乐的地方”,“为了到群众中去了解大众的文学”,那时,她在周文的陪同下,到自己到上海后从未去过的大世界专门去做调查研究;同时,她还“到书摊上去买大众唱本来研究”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丁玲对大众审美趣味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丁玲此期创作较之早期在形式层面发生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变化: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丁玲对大众审美趣味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丁玲此期创作较之早期在形式层面发生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变化:
一、在描写手法上,她极大地增加了行为描写的比重。这一变化,在她是非常自觉的。在上述“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的总结中,她强调“不要发议论,把你的思想,你要说的话,从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出来”,所表露出来的就是对行为描写的偏重。虽然她此期没有一概撇弃心理描写而不用(如《水》第一章对龙儿“黯黯的情绪”和《消息》起首对老太婆“被漠视的悲哀”的描写等,就均用了心理描写手法),因此,在这意义上,我们还不能泛泛地说,丁玲此期创作在手法上就全是“从死静的心理的解剖,进展到群众的连锁的活动” 、它所使用的“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
、它所使用的“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 ,但是,二者相比,重心却显然在行动描写上。如《夜会》对工人爱国热情的揭示,主要就是借助于工人李保生组织“九·一八剧社”演出前后工人们的一系列言语和行动的描写。《奔》对那群农民之觉醒过程的展现,所依托的也主要是他们先是因农村破产奔向城市谋求出路、后因城市失业严重又决计奔回农村与地主展开斗争的这一前后相续的行为之描写。
,但是,二者相比,重心却显然在行动描写上。如《夜会》对工人爱国热情的揭示,主要就是借助于工人李保生组织“九·一八剧社”演出前后工人们的一系列言语和行动的描写。《奔》对那群农民之觉醒过程的展现,所依托的也主要是他们先是因农村破产奔向城市谋求出路、后因城市失业严重又决计奔回农村与地主展开斗争的这一前后相续的行为之描写。
二、在句式句法上,她化繁为简,力求朴实和浅明。丁玲在早期创作中,为了对千思百结的人物心理展开曲折回环的描写,好用句法结构复杂的长句。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结尾处就这样写道:“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此段文字只是一句话,其中不但套有多个从句,而且在中心词前后又加上了许多修饰成分。其表意虽绵密,但在旁逸斜出中又使语言显得凝涩,而不够平易顺达。而到这一时期,在写作《水》《消息》《夜会》《奔》时,她已自觉这种“欧化了的文章还是不好”,所以,开始“有意识地想用中国手法” 来写作。这样,就导致了其语言上一个巨大变化的发生。在创作《母亲》时,她说过,“像我过去所常常有的,很吃力的大段大段的描写,我不想在这部书中出现”
来写作。这样,就导致了其语言上一个巨大变化的发生。在创作《母亲》时,她说过,“像我过去所常常有的,很吃力的大段大段的描写,我不想在这部书中出现” 。这种现象不但没有出现在《母亲》中,而且也没有出现在她此期所作的其他作品中。“他们正睡着,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怜的却是荒唐的梦”——这段文字在《奔》结尾处,所描写的是坐着火车去上海谋生的又一批“乡下人”的情状。它用的全是短句,推进很快;句中亦删繁就简,所用修饰词很少。早期作品中那种七宝楼台式的繁冗句式在这里确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朴实简约的句法和文体。
。这种现象不但没有出现在《母亲》中,而且也没有出现在她此期所作的其他作品中。“他们正睡着,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怜的却是荒唐的梦”——这段文字在《奔》结尾处,所描写的是坐着火车去上海谋生的又一批“乡下人”的情状。它用的全是短句,推进很快;句中亦删繁就简,所用修饰词很少。早期作品中那种七宝楼台式的繁冗句式在这里确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朴实简约的句法和文体。
总之,丁玲此期创作以“用大众做主人”“替大众说话”的内容追求和浅切易懂的形式追求,大力践行了“文艺大众化”的创作原则。也正因乎此,她的创作成了左联提倡的“新的小说”的代表,在左翼文坛大众化创作潮流中发挥了重大影响,她本人也因此荣膺了“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的美誉。
的美誉。
综上所述,在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丁玲积极响应“左联”号召,以自己的多重身份积极投入其中,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为这一运动的开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在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探索上,丁玲借助于《北斗》所刊两次征文和相关理论文章,或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自己的“意图”,体现了其理论认知的深度。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一方面,丁玲以“左联”领导和“左联”机关刊物主编的身份,积极开展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和壁报运动,大力培养以“工农兵作家”为重心的“青年群众作家”;另一方面,她又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躬身于创作实践,以“用大众做主人”“替大众说话”的内容追求和浅切易懂的形式追求,创作出了一批践行“文艺大众化”创作原则的作品,在左翼文坛大众化创作潮流中发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