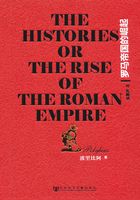
壹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有关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史集中在所谓的阶层(ordo,复数ordines)斗争上。当罗马共和肇始之初,公民分为称为patrician的世家贵族以及plebeian的一般平民两个阶层。patrician的世家贵族代表一个因出身而有权力去进行占卜吉凶、确知神意的宗教行为(这称为taking auspices),而因为他们有权进行占卜吉凶,这让他们能够占有“统帅权”(imperium)的职位。而这有“统帅权”之执政官(consuls),其权力由在执政官前导、拿“法西斯” 的仪杖队(lictors)来象征其权力。这是一种社会及法律的身份,而非经济阶级。执政官是世家贵族的囊中之物,平民阶层则被排除在外。但在最初时,世家贵族似乎容许少数平民家族加入,这可由罗马人树立在卫城神庙之前,所编辑历年来执政官名字的“榜单”(fasti)得知,但不久之后则封闭这一渠道。
的仪杖队(lictors)来象征其权力。这是一种社会及法律的身份,而非经济阶级。执政官是世家贵族的囊中之物,平民阶层则被排除在外。但在最初时,世家贵族似乎容许少数平民家族加入,这可由罗马人树立在卫城神庙之前,所编辑历年来执政官名字的“榜单”(fasti)得知,但不久之后则封闭这一渠道。
在四九四年,平民阶层的人要求进行社会及经济改革,包括取消债务及因债务所造成的奴役,还有法律上的不公行为,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于是集体退出罗马到附近的甲奴库伦(Janiculum)山丘,形成自己的“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 选举保障自己权益的护民官(tribunes plebis)。
选举保障自己权益的护民官(tribunes plebis)。 平民会议可以通过“决议”,
平民会议可以通过“决议”, 但只对平民出身的公民有约束力,因为它不是法律(lex)。因为当时流行在地中海世界的以民兵为主的步兵也已经在罗马发展一段时间,所以平民阶层的人力对当时刚成形的罗马共和极为重要,因此世家贵族被迫让步。让步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平民所形成的会议及选出的护民官被承认,虽然他们的功能仅局限在平民阶层而已。护民官有所谓的“护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可以干预纷争(intercessio),保护平民免于世家贵族的欺凌;平民也宣誓维护护民官的人身神圣(sanctitas)不被侵犯。在国家政务上,护民官有否决权,但这经常运用在否决军事动员,迫使世家贵族的阶层让步上。
但只对平民出身的公民有约束力,因为它不是法律(lex)。因为当时流行在地中海世界的以民兵为主的步兵也已经在罗马发展一段时间,所以平民阶层的人力对当时刚成形的罗马共和极为重要,因此世家贵族被迫让步。让步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平民所形成的会议及选出的护民官被承认,虽然他们的功能仅局限在平民阶层而已。护民官有所谓的“护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可以干预纷争(intercessio),保护平民免于世家贵族的欺凌;平民也宣誓维护护民官的人身神圣(sanctitas)不被侵犯。在国家政务上,护民官有否决权,但这经常运用在否决军事动员,迫使世家贵族的阶层让步上。
类似的危机又发生在四五一至四四九年,主题则是法律及其明文化(codification)。当时罗马遣使到希腊考察法律的发展,在回国后克雷苏斯(Appius Claudius Crassus)领导一个十人小组(Decemviri),暂停正常体制,对法律进行编修,后来发表“十二木表法”(Twelve Tables)。类似立法行为在希腊则是所谓“立法者”(nomothetes)的责任,往往发生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立法者”被授权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革;立法行为本身则是掌控这项资源的贵族对平民的让步。但在罗马,这十人小组中的部分成员趁机揽权,不愿退让,最后被推翻。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陆续发生创造可由平民阶层参与的官职,如市政官(aediles),出现取消债务以及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世家贵族阶层愿意部分退让,平民阶层也愿意接受妥协。
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三六七年。 因为阶层斗争所关系的是权力,而官职,特别是执政官一职,是权力的具体化。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获得让步:两位执政官至少必须有一位平民出身。但是世家贵族阶层则另外创造出一个专司法律事务的官员职位叫“副执政”(praetor,亦享有“统帅权”),同时开放给两个阶层,来弥补他们所丧失的权力,因为贵族在竞争官职上仍然占有优势。这种双方妥协让步、求取两边都能接受的中间点,是到当时为止改革的特色。在三〇〇年罗马通过“欧居尔尼亚斯法”(Ogulnian Law),将世家贵族阶层所垄断的占卜吉凶、探询神意的特权完全废除,宗教团体的位置也完全开放给平民。
因为阶层斗争所关系的是权力,而官职,特别是执政官一职,是权力的具体化。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获得让步:两位执政官至少必须有一位平民出身。但是世家贵族阶层则另外创造出一个专司法律事务的官员职位叫“副执政”(praetor,亦享有“统帅权”),同时开放给两个阶层,来弥补他们所丧失的权力,因为贵族在竞争官职上仍然占有优势。这种双方妥协让步、求取两边都能接受的中间点,是到当时为止改革的特色。在三〇〇年罗马通过“欧居尔尼亚斯法”(Ogulnian Law),将世家贵族阶层所垄断的占卜吉凶、探询神意的特权完全废除,宗教团体的位置也完全开放给平民。 在二八七年时,罗马又再度发生平民集体离开罗马的情形,最后由独裁官侯田希亚斯(Hortensius)通过称为侯田希亚斯法(Lex Hortensia)的法律,规定由平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具约束力;
在二八七年时,罗马又再度发生平民集体离开罗马的情形,最后由独裁官侯田希亚斯(Hortensius)通过称为侯田希亚斯法(Lex Hortensia)的法律,规定由平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具约束力; 另外平民对任何判决都有上诉平民会议的权力,以防官员滥权。这一法律的出现时常被认为象征阶层斗争的结束。
另外平民对任何判决都有上诉平民会议的权力,以防官员滥权。这一法律的出现时常被认为象征阶层斗争的结束。
被波里比阿指责为群众煽动家、在特雷西米尼(Trasimene)湖败给汉尼拔的执政官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便曾在二三〇年代以护民官身份主持平民会议,通过法律,将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Cisapline Gaul)的一些公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公民;在二世纪所谓的格拉古兄弟(Gracchi)改革,所利用的宪政武器便是护民官召开平民会议,通过对所有罗马人都具约束力的法案,来对抗以元老院主导的政治集团,最后逐渐衍生出所谓的“群众派”(Populares)及“贵族派”(Optimates,“最好的人”)。这些是未来的发展,在通过侯田希亚斯法时,这未来的发展是否在侯田希亚斯的心中,自然不得而知。
所以阶层斗争主要环绕在对官职及其所代表之权力的争取,特别是具有“统帅权”的职务,因为担任这职务会让持有者成为贵族,甚至致富,名留“榜单”,名垂千古。而整个家族最先得到这官职的人会成为政治上的“新人”(novus homo),使整个家族名列贵族之中。随着扩张的区域越来越大,一些官职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执政官在共和时期始终保持两位。有些时候,卸任官员会被元老院要求继续为国效力,而将其原来的“统帅权”继续延长,这称为prorogatio。在波里比阿《历史》里时常会出现如pro-consul或pro-praetor的官衔,其意为“行执政官”或“行副执政”之统帅权的延任官员。
回顾整个罗马早期共和最重要力量的阶层斗争演化,其过程大致平和,没有内战或流血,这让身陷晚期共和惊涛骇浪政争的西塞罗(Cicero)十分羡慕,因为晚期共和便是以格拉古兄弟的流血丧命开始。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高度的妥协性格,愿意求取双方都能接受的变化,力求社会共识,平民阶层的人虽然因此有机会分享权力,但世家贵族的阶层在这些让步过程中,也吸收平民阶层中最具才干的人员进入,最后在三世纪初逐渐浮现出“新贵族”(nobiles)。所以在侯田希亚斯法通过时,新的精英阶层也恰好形成。这些新旧贵族往往会建立联姻或收养的社会关系,因此元老院是个“寡头”且相对封闭的机构。但正是这新的领导阶层领导二六四年之后中期共和的海外扩张。
这种寡头的情形可以由数字来证明。在三六七年到四六年之间罗马有六百四十多位执政官,其中只有二十一次是由十一位“新人”所担任。何以如此?或许与罗马的社会结构有关,因为罗马上层与下层之间常以一种“保护主—随从”(patron-client)的社会关系所架构,而这关系定义上下彼此的权利义务,例如在选举中随从要为其保护主出钱出力,在保护主婚嫁中,贡献一部分嫁妆;保护主则必须照顾随从的利益,在困难时提供协助。波里比阿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即是这样的关系,虽然波里比阿是外国人。但是史家也提到其同时代之罗马年轻人会争相向豪强贵族致意(salutatio),即是这种关系的表达方式之一。 而这种关系可以继承,会被所谓的mos maiorum
而这种关系可以继承,会被所谓的mos maiorum 所强化,其深度可以由所留下的碑铭来证明。这种关系后来甚至延伸至海外,所以那些到罗马元老院求情的人(经常是之前被其征服的),时常会先去拜会他们的保护主,争取他的支持及保护。这种“保护主—随从”之间的社会关系时常使外人不容易打进贵族圈之中。
所强化,其深度可以由所留下的碑铭来证明。这种关系后来甚至延伸至海外,所以那些到罗马元老院求情的人(经常是之前被其征服的),时常会先去拜会他们的保护主,争取他的支持及保护。这种“保护主—随从”之间的社会关系时常使外人不容易打进贵族圈之中。
但正因为罗马实际统治的权力集中在这些数量极为有限的贵族保护主手中,所以一般公民权虽然包括参政权,但其真正效果其实有限,因此罗马人较愿施舍公民权给外人,因为公民权的行使并不会那么直接影响政治权力分配。这与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可以进行决策,分享城邦里的所有资源相当不同,所以希腊人十分吝于将自己的公民权扩大来与其他人分享。对公民权的不同看法以及实际运作,部分解释了希腊城邦何以一直维持小规模的社区形式,而罗马虽最初为一城邦,但却发展成近乎百万人的城市,并控制相当大的帝国。另外,罗马正是凭借这样性质的公民权,得以建立以下要提的意大利联盟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