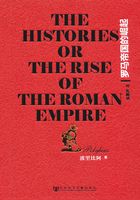
叁 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
罗马虽然是个善于政治组织以及讨伐征战的民族,但并不是很会反省自己对别人做了何事以及别人如何感受。这一连串的征战以及胜利对他们而言,仿佛是自然界的秩序:神明的力量以及他们的虔诚(pietas)保证他们的成功,而成功又证明眷顾罗马的神意。在这时期虽然他们扩张征服的对象包括高卢人,但其他的常都是在文明上更为先进的民族,所以类似公元十九世纪“白种人负担”的“使命感”,大概还不存在。但对罗马人而言,征服高卢人仍是为自保、掠夺以及致富,因为高卢人近在咫尺。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问一下:波里比阿所描绘之中期罗马共和的扩张(特别是针对希腊化世界)是否为帝国主义的行为?
公元十九世纪德国罗马史学家蒙森(Theodore Mommsen)提出“防御性之帝国主义”(defensive imperialism),认为罗马的扩张行为其实是一连串的预先防范的自保行为,而这是源自于三八六年高卢占领罗马以及后来汉尼拔蹂躏意大利。这听起来像是在为某些行为找借口辩护,就像他为当代殖民主义者所做的说辞之一。至于罗马人会派遣叫fetiales(单数fetial)的祭司到边界去,以规定格式宣告罗马的冤屈及补偿,然后在未得到适当回应时,会将一支矛丢掷到敌人疆域,请神明见证的仪式,为自己的战争行为争取神意的许可。 这绝不能解释说罗马的行径不是帝国主义般的;反而是将神明找来背书。
这绝不能解释说罗马的行径不是帝国主义般的;反而是将神明找来背书。
格吕恩(Erich S.Gruen)从法理及军事占领来讨论“帝国主义”。他认为即使在二世纪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也都还称不上“帝国主义”,而后来马其顿设省,是不得不为。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哈吕斯(W.V.Harris):他基本上是根据古典史家,如修昔底德,认为如雅典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永远不满意现状,总要求更多的现象,在希腊文叫pleonaxia。罗马就他而言,其扩张就是pleonaxia使然,而这是因为罗马社会原本就是极为好战,精英阶级之中的激烈竞争是以战功来衡量成就。奥古斯都在他的《神圣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Res Gestae Divi Augusti)提及罗马两面之神耶奴斯(Janus)神庙在罗马战争期间会打开庙门,关门则代表罗马世界普世太平,而耶奴斯神庙在罗马历史中第二次关门是在他任内。换言之,罗马的整个历史终究是不断地战争;和平反而是异常。另外,之前已经提及之“意大利联盟”本质上就是以战争来获利的军事动员机制,而罗马为“超级大股东”所形成的“企业”,必须以战争及胜利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很多人甚至怀疑:罗马的扩张行为在古代世界恐怕不是单独现象或是异数;其不同之处或许在它是如此迅速、如此有效、如此大规模以及如此成功。
但讨论这样的问题有其盲点:执行帝国主义行为的人不太常承认自己如此,而这又常涉及如何定义“帝国主义”这名词。格吕恩及哈吕斯的不同见解,部分正是根源于此。但就那些非罗马的国家,无论是曾经被其击败者(叙利亚王国)或是其盟邦(帕加马王国),或是没有太直接关系者(如比提尼亚王国),它们又如何看待罗马?因为没有“受害者”,又何来“帝国主义”?他们的资料都是集中在一六〇及一五〇年代,所以态势应该相对明显。罗马即使在那时候实质占有的地方仍多局限在意大利波河平原、西西里及撒丁,所以军事占领不一定是罗马成为“帝国主义”的要件。这些资料有两则是出自波里比阿, 但不在译文之中,另一则是碑铭。
但不在译文之中,另一则是碑铭。
如果我们有更多更早的资料,或许对所谓罗马“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便会理解更多。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从罗马如何仲裁亚该亚联邦与并入联邦后之斯巴达的冲突,还有菲利普五世在色雷斯扩充时, 屡屡遭受投诉,屡屡仲裁失利中,感受希腊人(无论是盟友或战败者)对罗马的行为敢怒不敢言。但以下三份年代稍晚的资料应该更清楚地透露出希腊人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看法,特别是这三份资料都在波里比阿第三书四章中被提及,他想把原来《历史》从二二〇到一六七年的范围延伸到一四六年,而一六七至一四六年对波里比阿而言的意义是:“因此本书之最后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入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波里比阿所谓的统治在法理上并未发生,因为这些国家仍有自己的君王及军队,但这三份资料所透露出的处境,则似乎有雷同之处。以下讨论顺序是依这三份资料的年代先后。
屡屡遭受投诉,屡屡仲裁失利中,感受希腊人(无论是盟友或战败者)对罗马的行为敢怒不敢言。但以下三份年代稍晚的资料应该更清楚地透露出希腊人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看法,特别是这三份资料都在波里比阿第三书四章中被提及,他想把原来《历史》从二二〇到一六七年的范围延伸到一四六年,而一六七至一四六年对波里比阿而言的意义是:“因此本书之最后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入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波里比阿所谓的统治在法理上并未发生,因为这些国家仍有自己的君王及军队,但这三份资料所透露出的处境,则似乎有雷同之处。以下讨论顺序是依这三份资料的年代先后。
安条克四世发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一七〇至一六八年)已经在之前论及。这战争的发生时间恰好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部分重叠,而罗马在一六八年由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二二八至一六〇年)接任统帅前,战事十分不顺,所以当安条克四世攻到埃及边防要地培留西温(Peleusium),即将以托勒密六世(一八一至一四五年在位)之舅的身份接管埃及时,恰好传来马其顿战败,罗马特使莱纳斯(Gaius Popilius Laenas)等人已到达培留西温的消息。安条克四世年轻时曾经在罗马当人质,与莱纳斯是旧识,在见到时趋前致意,但莱纳斯没有回应,只交给他一份元老院命令的蜡版,要他先读完再说。国王读完,回答说他必须询问他的国政顾问有关这些新的发展。莱纳斯并没说话,而是以一根葡萄藤蔓的枝干在国王周围画一个圈子。接着波里比阿又说:
(莱纳斯)告诉他在踏出这圈子之前要先回应这个信息。国王对这样的傲慢深感震惊,但在迟疑些许时间后,说他愿意做任何元老院要求他做的。在那时候莱纳斯及其同事才和他握手,并且有礼地欢迎他。元老院命令他立即结束与托勒密的战争。所以在指定的数日之内,安条克将军队撤回叙利亚,对所发生之事大为沮丧,但却必须向现况低头。莱纳斯及其同僚在亚历山大进行调解,敦促国王们要保持和谐。指托勒密六世及托勒密八世之间的冲突。以这种方式罗马人在埃及濒临毁灭之际,拯救了托勒密王国。
接下来波里比阿引进命运女神来说这时间的巧合,因为这是史家常提及的议题,所以在此顺便引用:
命运如此安排有关佩尔修斯及马其顿人的事情,所以在亚历山大及整个埃及被逼迫到绝境时,因为佩尔修斯的命运先被决定这事实而得到解救。假如这没发生或是尚未确定,我不相信安条克必然会遵守这样的禁令。
这些文字十分出名,他显示出罗马仅凭三位特使,便可以外交方式来执行元老院的意志,不费一兵一卒,不仅逼迫叙利亚国王撤军,而且也可以调解托勒密兄弟的争执。虽然史家也怀疑若非时间巧合,安条克恐怕不会撤军,但这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假设。之后安条克四世或许为了在国人或邻国面前扳回一城,恢复颜面,所以在一六六年于首都安提阿近郊达福奈(Daphne)举行盛大阅兵游行,展示国力, 但立即引来罗马元老院派委员会的调查,最后虽然无事,但罗马在犹太人叛变时却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刻意削弱叙利亚王国。之后德米特里欲返回叙利亚接任王位,元老院不愿让成年、充满活力的德米特里回国,宁可见到叙利亚由幼主当政,让国务陷入混乱,最后德米特里只好被迫逃离罗马返国。
但立即引来罗马元老院派委员会的调查,最后虽然无事,但罗马在犹太人叛变时却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刻意削弱叙利亚王国。之后德米特里欲返回叙利亚接任王位,元老院不愿让成年、充满活力的德米特里回国,宁可见到叙利亚由幼主当政,让国务陷入混乱,最后德米特里只好被迫逃离罗马返国。
第二份资料则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一年。小亚细亚西北的比提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二世(Prusias II),虽然是佩尔修斯的妹婿,但在战争期间骑墙等待战事结果。但是从罗德岛被如何对待的经验,可显示出罗马已经将任何不积极表态以及全力贡献的国家视为不忠及敌对,所以普鲁席亚斯不得不亲自前往元老院致意。波里比阿如此形容他在罗马的行为: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国王普鲁席亚斯到达罗马向元老院及将军们恭贺他们的胜利。他的行为完全不配他国王的身份地位,如我们可从以下之事来判断。首先当罗马使者来访,他将自己剃头来迎接他们,戴上白色瓜皮帽,穿上罗马公民服(toga)以及鞋子,简言之,就是将自己装扮成最近刚获公民权的解放奴隶(罗马的词语叫liberti)。在欢迎使者时,他高声宣布说:“我是你们的解放奴隶,我要做任何事来讨好你们,要模仿你们的习俗。”实在难以找到比这更没尊严的说话方式。 当在进入拜见元老院的场合时,他停在面向会场的门槛,垂下双手,对地板及就坐的元老致敬,说出:“万岁!我的救主神明!”几乎无法能够有更没志气以及更像女人的薄弱以及卑屈。他在会见时与元老所说的话在语调上也相似,所以转述甚是不妥当。在以一种完全令人鄙视的方式行为后,他正因为那种理由而得到同情的回复。
当在进入拜见元老院的场合时,他停在面向会场的门槛,垂下双手,对地板及就坐的元老致敬,说出:“万岁!我的救主神明!”几乎无法能够有更没志气以及更像女人的薄弱以及卑屈。他在会见时与元老所说的话在语调上也相似,所以转述甚是不妥当。在以一种完全令人鄙视的方式行为后,他正因为那种理由而得到同情的回复。
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例子,或许跟当事人的人格特质有关,但是那种恐惧,以及不惜卑躬屈膝,以求保全一切,令人印象深刻。
对极为讲求体面,而且也曾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出兵协助的帕加马王国,些许的独立政策,即使是有限的规模以及在自己后院发生,都还必须考量到罗马的因素。接下来这资料是封私人书信,内容显然不宜公开,不像其他还是会预设公共观众的希腊化时代的一般私人书信。它大约订年在一五六年,亦即阿塔罗斯二世在位初年。这是帕加马国王与佩西奴斯(Pessinus) “神殿国”(temple state)祭司阿提斯(Attis)的来往书信,讨论要如何一起遏止经过百年还在肆虐、几乎是所有人公敌的加拉太人。帕加马国王首先向阿提斯致意,并且说明他之前与大臣在另外一地所得到的结论。回国后他再将此事交付议论,结果大臣及顾问皆同意之前的决议,唯有一个叫克罗鲁斯(Chlorus)的人独排众议,坚持要先征询罗马人。当时没有什么人附议,但是当一再琢磨时,他们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国王的逻辑是:
“神殿国”(temple state)祭司阿提斯(Attis)的来往书信,讨论要如何一起遏止经过百年还在肆虐、几乎是所有人公敌的加拉太人。帕加马国王首先向阿提斯致意,并且说明他之前与大臣在另外一地所得到的结论。回国后他再将此事交付议论,结果大臣及顾问皆同意之前的决议,唯有一个叫克罗鲁斯(Chlorus)的人独排众议,坚持要先征询罗马人。当时没有什么人附议,但是当一再琢磨时,他们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国王的逻辑是:
假如成功,结果必然是嫉妒、不悦及怀有敌意的怀疑,正如他们(指罗马人)之前对我兄长所表现的。
这里所提及的是因为欧迈尼斯二世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没有表现出彻底的积极,所以当加拉太人在一六八年对帕加马王国发动攻击后,罗马在次年开始间接鼓励加拉太人继续作乱;即使欧迈尼斯打败他们,罗马人还是在一六六年给予这群行径如盗匪或恐怖分子的人自主的地位。阿塔罗斯继续说:
但假如我们失败,那注定毁灭。因为他们必然不会动一根指头协助,而是满意地旁观,因为我们进行如此大的计划时,却没征询过他们。但假如我们遭逢任何挫折(但愿老天不让它发生),我们会因为得到他们的应允之后才行动,而得到协助,而且也可以在神明善意的庇佑下,进行反击。我因此决定要在每个场合都派遣特使持续地去报告不确定的案子,而我们自己要做谨慎的准备,以备需要之时,能够自保。
从一九六年福拉明尼纳斯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宣布希腊自由解放,以及在一九四年他在与希腊人讨论从希腊枷锁撤军时,罗马驻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科林斯卫城,行军返回意大利,那是段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蜜月期”。但三四十年后,则令人觉得沧海桑田。在上述这些地方都没有罗马驻军,但现在罗马仅凭特使或命令或只是当事人臆测罗马可能会如何反应,罗马意志便被遵守;另一方面,罗马人甚至会做出一些对当地人不利的决定,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所以当罗马宣布提洛岛为自由港,罗德岛贸易立即一落千丈,无法再维持海军。所以要评论中期罗马共和的扩张是否为帝国主义,或许从这些接收端来看,可能比较具体,因为帝国主义加害者总必须要有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