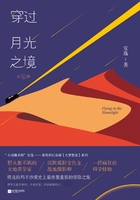
第11章 蜜月期与雨林
“我想活得像棵沙枣树,哪怕外表丑陋毫无美感,千里之外的沙漠蜂也能被它吸引到跟前。这才是招蜂引蝶的最高境界呢!”
——程旷
接下来的七天,很快过去。
上帝创造世界也不过用了七天。
在沙漠里过日子,昨天与今天并无区别,今天与明天差别也不大。在程旷眼中,七天不过是一眨眼。
而对于陆晋来说,这样毫无波澜的生活,却好像梦一样恬静。
他每天跟着程旷进进出出,看她在实验室里伏案描绘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纹图,或者彻夜不眠地处理采集的样本。
有时,他会一整天扶着她紧实的腰,跨坐在越野摩托的后座上,迎着干燥劲烈的风,随着沙丘的起伏,穿梭在深深的丛林中……
有时,他会跟着她徒步去牧区,给骆驼、羊群密集放牧后的土地取样做对比。又或者,一群人挤在丁克的房间里,给他出谋划策,陪他在网上与那个叫“多肉植物不吃素”的姑娘耍贫嘴。
整整七天,除去睡觉,陆晋与程旷形影不离。
对于陆晋来说,与一个人如此亲密,这是人生中独特的体验。
对于程旷来说,这七天却并不好过。
她向来独来独往,很不愿意随时拖着个累赘。
十年来,她早已习惯与自己相伴,孤独是她生活的常态。
她一面要集中注意力处理手头堆积如山的样本,一面要全力以赴地分析找水仪绘制的地底剖面图。同时,她还得看紧陆晋,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这令她浑身不自在。
然而,陆晋这个人存在感极低。他好像有种特别的本事,能把自己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渐渐地,她开始习惯陆晋的存在。不,应该说是忽略。
她常常忘记陆晋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像一个时刻在呼吸的人,反而忘记了呼吸一般自然而然。
第八天。
一出房门,陆晋便觉得空气里有什么地方与昨天不一样了。
他凝神向远处眺望,想要寻找那异样来自何处。
浓荫起伏,蓝色的天高而远,像冬天结冰的湖面,薄脆剔透。
一切都那么平静,平静得没有丝毫异常。
这依然是绿岛基地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程旷匆匆赶到的时候,陆晋正悠闲地坐在食堂的大树下,将馍馍掰碎了泡在羊奶里,好似他不是坐在酷热的大沙漠里,而是在清凉怡人的咖啡馆。
看着陆晋平淡安然的眉眼,程旷心中一动,突然不想那么早去面对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她一屁股坐到陆晋身边:“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陆晋挑眉。
他话很少,但不知为什么,一周下来,程旷已经摸清楚他的微表情。
“从今天开始,基地进入Honey Moon(蜜月期)。”程旷眉开眼笑。
早上起来,她一察觉到空气中的那点异动,原本紧绷的情绪忽然就缓和下来了,好像未来的一切忐忑不安,未知的扑朔迷离,都在那点与往日不同的异常里得到了安抚。
陆晋被她的笑容晃得眼花,直觉告诉他有非常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他。
他轻轻含住那句“Honey Moon”,嘴里像被人塞进了一颗橘子糖。
程旷领着陆晋,往密林深处走去。
她是个急性子,走路风风火火,每一步都尽可能迈到极致。可今天她一反常态,施施然然仿佛散步一般,沿着林间小路向湖边缓缓前行,样子颇为享受。
“你要带我看什么?”陆晋看着始终笑嘻嘻的程旷,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问道。
“不是看,是——”程旷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然后做了个深呼吸的动作,“你没发现,今天空气里有点不一样吗?”
陆晋微眯起眼,深深吸了口气:“好像——”
他发现,越往树林深处,空气便越发清冽甘甜。
空气里飘荡着一股甜蜜的气息,似有若无,好像几分钟前才有一个涂了香水的女郎从这条路走过。
程旷见陆晋略微困惑的表情,得意地笑了,不由得急性子又上来,一把拽住陆晋的手腕道:“走吧,别磨蹭了,马上就到了。”
陆晋被程旷猛地一拽,踉跄了一下,跟着她疾步前行。
沙地上阻力大,本该举步维艰,可是这一路,被程旷抓着手腕连拖带拽,不知是因为她的力道,还是她扣住他的手腕的奇异触感,陆晋觉得轻松了不少。
两人攀爬过一片起伏的灌木小丘,空气里的香味越发浓郁。
再向前,那香味似乎变得有形有质,闭上眼,会有种空气都是金灿灿的错觉,挥手一抓,就能捞一把浓稠的蜂蜜,眼、耳、口、鼻、仿佛每一寸肌肤都浸泡在无穷无尽的蜜糖中。
“看!”程旷忽然停下,随手向前一指。
陆晋凝神望去——眼前是一大片沙枣林,褐红色的树干遒劲扭曲,贴地斜斜地生出去,尽管树干干燥皲裂,像老农操劳过度的手,毫无美感,但蓬蓬密密的枝叶遮住大半天幕,银灰色的叶片长长的、扁扁的,像一只只纸折的扁舟,又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这些天,陆晋跟着程旷在基地里穿梭,这样的树见多了,可是,今天好像有些不一样。
原来,沙枣树开花了。
重重叠叠的枝叶间,抽出一串串花穗。无数的沙枣花正含苞待放,似一把把合拢的绿色小伞,鼓鼓囊囊,好像下一刻就会“砰”的一声撑开来。盛放的花也不少,一团团一簇簇,散在枝头。
程旷凑到一枝低垂到额前的花穗前,那上面正开着七八朵喇叭似的小花。花茎自下而上,像白嫩的豆芽一般,直到顶端处才绽开黄澄澄的四片花瓣,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像金色的星星。
她忍不住闭上眼,深深呼吸,嗅了满满一鼻腔蜜香。她轻声对陆晋说:“沙枣花要开整整两个月,整个基地都像泡在蜜糖里,做梦都是甜丝丝的。”
难怪她说,这是基地的蜜月期。
陆晋微笑,一向简单粗暴的程旷,好像也在这连绵不绝的花香里,变得甜蜜柔软了。
谁知他念头刚起,程旷却匪气十足地拍了一下沙枣树粗糙干裂的树干,像在拍自己老友的肩膀一般,豪气干云道:“我呀,就想活得像棵沙枣树。哪怕外表粗糙、丑陋、拧巴别扭、毫无美感,却有极旺盛的生命力,哪儿都困不住它、难不倒它,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开出最甜蜜的花,结出甘香的果……”
是呀,真正有魅力的女人,绝不是徒有个好看的外表。
陆晋怔了一下,没想到满嘴荤段子的程旷也有正经的时候。
谁知程旷下一句话又将自己打回原形:“千里之外的沙漠蜂也能被它吸引到跟前。这才是招蜂引蝶的最高境界呢!”
“骑着马儿走过昆仑脚下的村庄,沙枣花儿芳又香,清凉渠水流过玫瑰盛开的花园……”少年清亮稚嫩的歌声在沙枣林深处响起。
两人循声望去,正好看见丁克带着艾尔肯在树下忙碌,十几个蜂箱散落在浓荫下,不断有腰身细瘦黝黑的蜜蜂穿梭其中。林子里安静极了,只有蜜蜂“嗡嗡”的声音,像轰炸机一般响彻其间。
艾尔肯和丁克都戴着帽子和面纱,熟练地将一片片台基插进蜂箱里。少年正放开嗓子,随着微微浮动的香味,唱着歌:“一个俊俏的姑娘正在静静的苇荡,美丽头巾随风飘荡,乘着萨它琴声旋转到我的身旁……”
“沙漠里居然也养蜂?”陆晋一边拍照,一边问。
“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都没有蜜蜂了。但是不养蜂,这么多植物开花得全仰仗人工授粉,还不把人累死?”程旷小声道,“人类所利用的一千三百多种作物中,有一千多种依靠蜜蜂传授花粉。如果蜜蜂灭亡,人类最多只能存活四年。可是现在全世界每年有30%的蜜蜂离巢不归,神秘失踪,连尸体都找不到。”
程旷见陆晋听得专注,又神秘兮兮地说道:“有人说,这是外星人为了占领地球使得诡计。它们把蜂群全部诱拐走了,人类就会自动灭绝。”
“别听旷姐胡说。”丁克走过来插嘴道,“这其实是‘蜂群崩溃紊乱’导致的。郊区城市化、农药和杀虫剂、滥用抗生素、气候变暖、电子产品的电磁波辐射干扰蜜蜂的导航系统……这些才是导致蜜蜂不断消失的真凶。”他一说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就变得滔滔不绝。
远处的艾尔肯一抬头,也看见了陆晋。少年立即热情地对着陆晋挥了挥手。深目浓睫的美少年,在嗡嗡的蜂群中,笑得格外灿烂:“大哥哥,等蜂子酿好蜜,我取了送给你。搁到羊奶里,甜得很!”
陆晋举起相机,镜头里便定格下少年淳朴的笑容。
“没想到死亡之海里,也能养活这么多蜜蜂。”陆晋看着花枝上忙碌的蜜蜂忍不住感叹。
丁克的声音忽然就有些低落:“这是岳老托了好多关系才从巴丹吉林运过来的一箱沙漠条蜂。他带着我们,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养出现在的规模,连酿好的蜂蜜他都舍不得吃一口,几乎都留给蜜蜂了。”
“都一个星期了,岳老还没回来?”见丁克主动提起岳川,陆晋乘机追问。
丁克目光一闪,直勾勾地盯着程旷,自己却不吭声。
“快了!处理好镇上的事情,他就回来了。”程旷瞪了丁克一眼,接口道,“呀,差点忘了告诉你,娄教授正带着人给雨林揭罩子,你要去看吗?”
“今天就揭盖了?”陆晋愣了一下。
彻底开放雨林,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是整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后一环。
如果雨林真能给沙漠带来雨水,整个“绿饵计划”就活了。相反,整个基地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它关系着基地所有人的命运。
陆晋有点迟疑:“你们不等岳教授?”
“等不了了。”程旷若有所指,“绿能集团已经把我们的研究经费全冻结了,再不出结果,我们就弹尽粮绝了。你难道不知道?”
陆晋默然。
程旷面上微紧,那只黑洞洞的眼罩显出几分森然冷意。
但随即她又叹了口气,怎么能怪陆晋呢?
他不过是个只能如实汇报的评估师而已。
可是,他真的是评估师吗?程旷眼前晃过好几个她接触过的环保测评师。
陆晋——和他们很不一样。
她心里不禁有些困惑。
丁克脱掉防蜂服,和陆晋、程旷一起,匆匆往小白楼旁的雨林赶去。等他们赶到,巨大的玻璃金字塔前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集了百来号人。现场一片嘈杂,甚至有牧民赶着羊和骆驼来凑热闹——莫名的,程旷想到了刚才见过的蜂群。
程旷挤过一大堆工人,她冲到最前面,一眼便看见了正在和人争论的娄云。
一向淡雅的娄云,今日打扮得颇为隆重,微卷的齐耳短发梳得一丝不苟,面上是比平日更精致的淡妆,豆沙红的唇膏衬得她小麦色的肤色格外精神。
然而,只有熟悉她如同程旷才会发现,她的唇瓣有些轻颤,手指紧紧地团在掌心,紧绷的指节有些发白。
娄云很紧张!
程旷挤到她跟前,施一源和裘胜见程旷过来了,也从旁边的树下走了过来,一行人团团将娄云围住。
娄云见了程旷,脸上一松,一把拽住程旷的手,声音有点抖:“小程,黄工他们刚刚发现,打开温室玻璃罩的联动轴是单向的。”
“什么意思?是没法打开了吗?”程旷心下一沉。
“能打开!”裘胜插嘴,“就是打开后,没法再关上了。”
“哦!只要能打开就行!”程旷松了口气。
娄云瞪了插嘴的裘胜一眼,继续忧心忡忡地说道:“万一罩子打开了,雨林和周围环境不能融合。眼看着一天比一天热,昼夜温差又那么大,要是它们适应不了沙漠气候死了……怎么办?”
“不怕!整整十五年了,如果它们还适应不了,只能说明我们的理论一开始就错了。驯养雨林植物适应沙漠气候是行不通的!”程旷斩钉截铁地说,一点也不顾及娄云的感受。
娄云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
“一旦打开温室,这些植物的命运,就再不是我能掌控的了,一切有可能会向着失败一步步迈进。”娄云喃喃道。
“怕什么?你不是经常说,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每证明一条路行不通,就代表离真理的路更近一步吗?”裘胜嘟嘟囔囔,“大不了就像旷丫头说的一样,证明雨林适应不了沙漠呗!”
“是啊,我这一生就参与了两个重大项目。第一项目失败了,证明人类无法复制地球。如果这次又失败,就证明人类无法改变沙漠气候。”娄云讪笑道,“难道我这辈子,就是专门给别人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当垫脚石的啊!”
“娄姨!昨天你不是还挺有信心的吗?”丁克挠挠头,想要安慰明显有点失态的娄云。
“昨天,我不是还想着,万一出了什么不好的状况,还能把温室重新关上嘛。”娄云惨笑。
“别担心,我一早就打了一卦,卦象极好!况且,理论上说——”施一源忙插一嘴。
“别理论上说了!”娄云打断他,“我的理论比你熟。”
施一源悻悻住嘴。
“娄教授,如果雨林活不了,其实你们也没有机会再来一次了。”陆晋冷静道,“一旦实验失败,项目直接就终止了。所以——”
“别无选择!”程旷接口道。
众人一默,气氛变得越发凝重。
这十五年里,他们把能做的都做了,已经耗尽心血,面面俱到了。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雨林活,基地活。
雨林带来雨水,“绿饵计划”第一阶段实验成功,后续计划将顺利推进。
而失败——不过是十五年青春空掷!
想到这里,娄云咬了咬唇,沉声吩咐:“打开吧!”
这句话她说得很慢,每个字咬得又准又重,像是要把十五年的时间、心血、期待都浓缩起来,注入这短短的三个字里。
负责基地基建和工程的黄工程师按下启动按钮,十几名机械工人相互协作,金字塔般的钢化玻璃开始轻微晃动,各连接处的连轴发出巨大的声响,巨大的玻璃罩子瞬时分崩离析,不断向外撑开、变形、折叠,变成一面面窗户大小的玻璃扇面……
娄云全神贯注,每打开一扇玻璃,她的心脏就紧缩一次,呼吸越来越急促,瞳孔不断收缩。
期待、紧张、忐忑、担忧、兴奋、不安……复杂的情绪在她脸上横陈变幻。
陆晋不动声色地按动快门,记录着眼前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丁克双手合十默默祈祷,裘胜抱臂仰望,施一源掐着手指念念有词。
而程旷笔直地站在娄云身边,伸手半搂着对方的肩。她像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牢牢扎根在地下,稳稳地为娄云提供依靠。
她抬头望着雨林,神情端庄肃穆,那唯一的眼睛里,宝光潋滟,在玻璃的反光中,亮得令人不敢逼视。
“轰——”一声巨响,沙地震动了一下,所有的玻璃罩子同时收拢,堆叠着重重压向地面。
与此同时,一股庞大潮润的植物气息如猛兽一般扑向众人,迅速向周围荡开。
那湿漉漉的水汽,在接触到阳光后,瞬间在空中折射出一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种色彩都是苍白沙漠里的奇迹。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皮肤上绵密的水汽与阳光交织在一起,带起阵阵凉意,陆晋的手臂上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那庞大的一弯彩虹,近到几乎触手可及。
程旷忍不住伸出手探向那道彩虹,她的手直直穿过彩虹,心情顿时被染成了彩色。
她回头,对着惊呆了的众人展颜一笑:“看!彩虹!这是吉兆吧!”
她话音刚落,那轻雾一般的水汽便被干涸的沙漠吸附了,彩虹氤氲开,变成一道浅淡朦胧的影。
“可以解释为吉兆,但也可以解释为,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施一源掐着手指,蔫儿蔫儿地回答。
“闭上你的乌鸦嘴!”娄云、程旷几乎同时大声呵斥。
整整一天,基地的人都沉浸在一种亢奋与忐忑交织的氛围中。
黄昏时,十座玻璃金字塔全部揭开了。加起来超过六十个足球场面积的雨林,彻底暴露在沙漠干燥劲烈的空气中。
不知是不是错觉,程旷觉得整个基地的温度都变凉了。
所有人都闲下来,只有施一源最忙碌,他忙着带领团队测量空气里的各项数据,温度、湿度、密度……
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带着助手赶往不同的地方释放系留汽艇,紧锣密鼓地展开各项监控。
除了最忙的施一源,其他人都久久徘徊在雨林中,不肯离去。
其实这些热带雨林,一直都在。
只是隔着厚实的玻璃罩,碰不了、摸不到,甚至感受不到那些青翠欲滴的颜色散出的淋漓酣畅的植物气息。
那笼中的神秘丛林,更像个华丽虚无的梦境。
可是现在,玻璃屏障被拆开了,一伸手就能摸到棕榈树巨大的、打了蜡一般光滑的叶片。一俯身就可摸到如丝绒般厚实的苔藓,一扇鼻翼,就能闻到白色兰花馥郁的香味。那些如蛇般妖娆缠绵的藤蔓,更是迈近一步,都有可能被绊上一大跤。
一瞬间,只可远观的人们,进入了这个湿漉漉的绿色梦境。
或者说,梦境终于照进了现实。
牧民、护林工人,甚至负责拆卸的工程师们,都傻愣愣地站在绿林边缘,忍不住趋上前去零距离接近这幽深丛林。
顽皮的畜生们也跟在主人身后,鬼头鬼脑地凑上前看热闹。
看着看着,一只憨厚鲁钝的黄骆驼,便忍不住吸了吸鼻子,肥大的鼻头在一片鲜嫩嫩的芭蕉叶上来回蹭了蹭,敦厚纯真的大眼睛上,茸茸的睫毛一眨,厚嘴皮一掀,白森森的牙齿啃上去,一截翠生生的叶尖“嘶啦”一声,进了它的嘴。
骆驼的主人准确地接到娄云的一记眼刀,吓到赶紧伸手拍了憨骆驼的脑袋一下,半生不熟的汉语囫囵着,急骂道:“小东西,又调皮。”
正在尝鲜的骆驼不防被打了个正着,不高兴地尥了蹶子。主人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下不来台,用鞭子抽了它的肥屁股一下,嘴里叨唠着,将一根绳上的一溜儿骆驼全赶走了,只留下驼铃清脆的余音。
此时,沙漠里的夕照如期而至,红彤彤的夕阳像刚从红色油漆桶里捞出来的,艳得耀眼。万事万物遇上这样朦胧而绮丽的光线都会变得柔情万种。
金色的光柱在叶与叶、枝与枝之间勾连的缝隙里穿梭,千束万束,如金箭般笔直地射下来,临到地上,腾起一片金色的烟雾。
娄云逆着光,站立在一片雾腾腾的霞光中,白发下的七情六欲都隐没在强烈的光线里。
初到沙漠时,她才三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华。
一开始,她只是顶着烈日,全心全意地给沙漠画格子、结草皮,全心全意地等着那毫无生命气息的砂砾中生发出土壤的生机和潮润。
这一等,便是两年。
两年后,她又亲力亲为,为那些沙土布下适合植物生长的菌群。
接着,那些被她精心挑选出来的雨林植物穿越重重障碍,被精心呵护着,来到这陌生的沙漠王国。
有的还稚嫩纤弱,有的嫩白根须上还带着另一个经纬度的泥土,有的还是团得紧紧的种子,有的已经被折腾得半死不活,有的雄赳赳等着征服全新的土地……她日夜不息地盯着,亲力亲为、鞍前马后,把它们全部妥妥帖帖地移植到这片干涸的沙地里。
之后的十余年,每一天她都过得小心翼翼,像照顾新生婴儿一般,照顾这些娇弱的生命。有的植物水土不服,活了几天便死了,变成同类的肥料;有的长了几年始终坚持有情饮水饱,被她忍痛淘汰了;有的感染了虫害,被啃成筛子似的;也有的植物受不了昼夜温差被摧残萎谢的……但终于,它们中有一半的伙伴扎下根活了下来,靠稀薄的水分挣扎成了林。
看着金光中近乎神圣的茂密雨林,娄云的眼睛湿了,一滴泪打着圈在眼珠上勾出炫光,喉头里慢慢涌上一点哽意。
十五年时间,匆匆就过去了。黑发怎么就染了雪?
蓦然回首,一切竟然短暂如几个碎片般的闪回。
在这些瞬间的闪回中,她失眠过、头痛过、号哭过、掏心挖肺般地难受过,她付出了所有能付出的感情,承担着连男人也不能抗住的重压。
没有亲人,没有伴侣,终生也不可能有人唤她妈妈,扑入怀里让她抱。
她孑然一身,在这漫漫黄沙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到了今日。
可是,看着眼前葳蕤的雨林,一花一叶一木一苔藓,都让她骄傲——一个母亲的骄傲。
程旷被娄云的神色震撼,一时间心中豪情涌动。
望着庞大的丛林和垂垂老去的女人,程旷耳边回响起娄云曾经说过的话:“谁说女人活着的价值就是生孩子?这世上多数人活得浑浑噩噩,生的孩子一生照样活得浑浑噩噩。所谓血脉延续,不过是用平庸的DNA复制平庸。就连所谓的亲情,三代以后的关系便淡如陌路。我又何必执着于此。不如用我有限的一生,去创造无限的生命。只要这片雨林在,我死了以后,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整个沙漠里的生命,都是我曾经活过的证明。”
这些话,好像又回荡在丛林间,回荡在这沙漠的上空,撞击着程旷的心。
生命如此短暂,可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创造永恒。
这永恒,可以是艺术,可以是宗教,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历史,可以是美,甚至可以是坚如磐石的信念,或是生命本身。
那才是她程旷应该追求的大道,而不是短命的爱情。
程旷仰起脸,迎着树梢间漏下的点点金光,嘴角微微扬起来。
她浑然不觉,有双眼睛正透过镜头洞察到,她平静表象下汹涌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