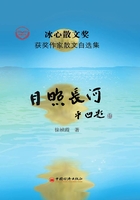
寻访上里
上里,是一个古镇,据说在三国时就有了。三国,该是多远的年代。一个跨越了无数个朝代,拥有1700余年历史的古镇,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我的心中便有了一份再也放不下的惦记与好奇。因了这份惦记与好奇,我决定去上里古镇探寻个究竟。
来到上里古镇,是一个雨后的清晨。空气格外的清新且湿润,到处弥漫着青草的气息和竹笋的清香,薄雾未消,绿意渐浓,车蓦然停驻,古镇已悄然在眼前——原来上里古镇竟然藏匿在大山深处,我的一个不经意,便与它撞了个满怀。
古镇并不小,这让我有些意外。一路行来,道路并不宽阔,也并未见车水马龙,山是宁静的,树是宁静的,水流也是宁静的,路上少有房舍和人家,一辆一辆的巴士不紧不慢地走着,像是在串门或是走亲戚,淡定与悠闲,并不似别的旅游景区那么喧闹沸腾。这让我有些窃喜,我可以不用受纷乱的干扰从从容容地打量和端详它了。
放眼上里古镇,我突然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上里古镇何尝不是隐匿在大山里的一个世外桃源,路之畔,古镇突兀而至,突兀得让人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在林之中,在水之岸,在路之侧,上里蓦然横出,陈列在你的面前,如一只待渡的船,静静地泊着,不加修饰,铅华不染,朴素而庄重,在淡定与安详中记录着一段时光的风雨与沧桑。
一大堆竹笋闯进我的视线,阵阵清香扑鼻而来,有的整齐地放在三轮车里,有的摆放在竹筐里,全都头对头,有序地排列着。起先,我并不知道这些竹笋堆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因为竹笋边并没有人。我心生疑惑,四处一瞥,发现一个胡须发白的老人和一个中年的妇人,两人待在离竹笋两米开外的地方,拢着手。意识到他们就是竹笋的主人,我笑了,轻轻地问,竹笋是卖的吗?妇人应着,是。我问,多少钱?女人低低地答,8角。我惊讶地说了一声,好便宜哦!因为,在以往的经验中,大凡景区的东西都是比较贵的,多数以盈利为目的,而且还有抢客拉客的现象,而眼前这两个卖笋人如此平静,如此淡定,全然不像是在做生意。他们的神情和他们的衣服一样朴素,陈旧的中山装和粗布的红花褂子。他们带着笋子来卖钱,但是身上依然褪不去山里人特有的质朴与憨厚,他们在等待着一份你情我愿的交易,买者心甘情愿地买,卖者心平气和地卖,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许正是他们——古镇世世代代生存的百姓让古镇依然朴素,依然庄重,因为朴素和庄重不仅是外在的表象,更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精神上的庄重才是永恒的庄重。
我深深地凝视了他们一眼,心里充满了欣慰。
真正走入古镇我才知道,上里古镇的出现远比三国要早,它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一个藏匿于深山里的小镇会有这么久远的历史,是我始料不及的,更是令我惊讶慨叹的。谓之三国,就已经很早,谓之西汉,唯有让人望镇兴叹了。在来四川之前,我没听过它的名,在来四川之后,我无数次听到它的名,很多人知道我是文化人,就鼓动我来看一看,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走走的地方。由好奇到惦记,由惦记到神往,由神往到终于下定决心来探寻一番,果然不负此行!
上里古镇,东接名山、邛崃,西接芦山、雅安,坐落在四县交接之处,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它以四川为起点,经云南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与西北丝绸之路一样,“南方丝路”对世界文明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史料记载,上里古镇初名“罗绳”,是取其昔日古道上的驿站、关隘之意,它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边茶关隘和茶马司所在地,还是红军长征北上的过境地。
初闻上里,让我好不惊奇,却不料在惊奇之余,它带给我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
踏入古镇,我的心也变得庄重起来,令我庄重的不仅仅是上里的建筑和风物,更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我是从一座桥上走进上里的,桥头立着一块本色的石头,石头稍显粗糙,凸凹不平,其上书写着“水墨上里”四个字,至此,古老的上里便在我眼帘里郑重地拉开了帷幕。
桥不宽,约三尺余,全部是由一米多长的石条铺就,石条的排列谈不上规律,但是却相当的平整,相当的稳当。雨后,水面有些混浊,到处泛着湿漉漉的气息,但并不影响古镇的庄重与沉稳。想来,这儿的水从来都是波平如镜,不管是泛着泥土的雨水,还是素日的一河清流,都是盈盈而充沛的。两岸的石阶上,到处泛着茸茸的绿苔和一些不知名的碎草,没有泥土,却依然能够鲜绿。我跳跃着走过石桥,临面而来的是两幢吊脚楼,一座是戏楼,一座谓之“近水楼”,两楼相向而立,穿巷而进,戏楼便郑重地进入我的眼帘。戏楼的正中赫然一幅川剧脸谱,它正庄重而肃穆地凝视着古镇来来往往的人流,好像在越过时空与人们做着某种交流。川剧脸谱是川剧的精髓,川剧的魂魄所在,它是不二的,它是四川独有的,这便是地域文化,唯有四川才有的特色。
狭长的石板街,苍老的吊脚楼,在我的眼前一顺儿排开,我的目光随着它一直向前延伸。上里古镇呈“井”字状分布,一条主巷,主巷两边分别有侧巷,一样的庄重,一样的古老,一样的刻满了岁月的印痕。上里很安详,没有叫卖声,没有哄抢抬价,店主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店铺里,人来不惊,人去不嗔,平静地看着来来去去的人,静静地问,静静地答,静静地交流,静静地买与卖,一切的一切,因为古镇的古老而从容淡定着。
我走进一家小店,那里专卖牦牛产品,有梳子、刮脸器、刮痧片、念珠等。店主是一个中年男人,我进店时,他正在整理被游客拿乱的物品,每一件依序归位,摆放整齐。见我走进,他冲我微微笑着,侧立一旁,并没有马上向我推销商品,只是任我自由地观看。我在店里转了一圈后,走到了摆梳子的地方,梳子有大的、有小的、有中号的。或许女人天性爱美,我对梳妆的物品情有独钟,拿起一把中号的梳子问他,这牛角梳多少钱?他温和地说,10元钱1把。这让我有些意外,这梳子怎么这么便宜呀!但我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声。我很爽快地掏出50元钱,买了5把,准备回去送亲友。听说用牦牛梳梳头可以美容养颜,送人应该不错,东西好且物美价廉,心情不由得愉悦起来。
我不知道这个男子可不可以代表古镇的生意人,但是这儿的许多生意人置身店里却不叫卖,有的在喝茶,有的在做手工,有的手捧一本书,有的在浏览网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平和与悠闲,一种淡泊名利泰然立世的生活态度。这儿少了大城市的喧嚣与浮躁,也少了大城市的急功近利。古镇朴素,人心也朴素,古镇沉静,人心也沉静,古镇端庄,人心也就有了一份端庄与从容。于是我在想,人是不是普遍都是受环境影响的生物呢?
当时,恰逢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此写生。上里到处都是一些支起画架写生的学生,河边、桥头、小径、古巷、木屋旁,一样的年轻,一样的认真,一样的投入,他们在用心地描绘,描绘一座古镇的风雨岁月,他们的年轻,显得上里愈发的沧桑与古老。走过他们身边时,我会忍不住停下脚步,驻留在他们身后,静静地观赏。他们中有描摹风景的,有画吊脚楼的,有写意小桥流水的。对于绘画,我虽不精通,因为喜欢,也略懂一点儿。我立在他们身后,看他们的一笔一式,有线条的勾勒,有颜色的渲染,有构图的比例。绘画是个考验人耐心和审美的活,需要勤奋,也需要天赋,当一张苍白的纸在他们的笔下渐渐地变得丰满而富有情趣时,画者的内心一定是很有成就感的。
一座古老的石桥吸引了我,吸引我的不仅仅是桥上那些写生的学生,还有桥上晾晒的竹笋。那些竹笋很白很鲜嫩,白亮亮地铺在竹席上,竹席用的年代久了,已经泛出棕褐色,它的沧桑与竹笋的嫩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在桥面耀眼地排开,强烈地刺着人的眼。四川不愧是个出竹子的地方,上里的竹笋及竹制品便可窥其一斑。桥上有晾晒的,河边的石坡上有晾晒的,街面上还有一簇一簇的人围在一起削竹笋,那些竹笋大且肥硕,形状酷似青笋。这些不同性状不同功用的竹笋,让上里与别的古镇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是无处不在的竹香气。
我在一群削竹笋的人旁边站定,用一个外来人特有的好奇观望着他们。他们当中,有年长的大嫂,有年轻的女子和媳妇,还有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都埋着头,忙着自己手中的活,有削皮的,有切片的,有切丝的,像是分了工。我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你们好,在削竹笋呀?他们抬起头,把脸一起转向我,一位年长的大嫂说,是呀,竹笋要削去皮才好吃呢!我说,这些竹笋都可以怎么吃呀?他们说,可以炒着吃,可以炖肉吃,还可以做成酱菜。我一听可以炖肉吃,顿时兴奋起来,可以炖些什么肉啊?年轻的媳妇答话了,炖鸡、炖排骨,还可以炖牛肉,都挺好吃的。我听后,立马有了想尝尝的欲望,就说,那你们这有吗?有的。大嫂回过我后,马上又说,我给你叫人去,看样子,那位大嫂就是这店里的老板娘,答过我之后,马上同店里招呼,有客人来了。
少顷,一个汉子从里间出来,将我们让进店里。店不大,却干净整洁,一律的木头桌椅。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份竹笋炖牛肉、一份丝带鸡,我们外点了一份清水豆花、一个木桶米饭。店主很麻利,一会儿,菜就端上来了,一句“你们慢慢吃”,他便退下了。我们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不错,确实不错,竹笋的清香伴着牛肉的醇香,既清爽可口又别具风味,这样的菜,可能只有在竹笋下来的季节才能品尝到,在别的时间,可能就尝不到这么原汁原味的竹笋牛肉了,新笋鲜脆嫩,而干笋就有点儿缺少水分,没有新笋的口感好。我庆幸,我们来的正是时节,既看到了这么别具风情的古镇,又尝到了这么可口鲜香的美味,眼福口福都算享上了。
走出店门,我依然意犹未尽。
一只狗摇摇摆摆地朝我走来,不知是嗅到了肉味,还是一贯爱悠然在街巷上散步,反正没有怕人的意思。它落落大方,步态从容,不紧不慢,穿行在行人和巷市之间,大有一种主人般的气定神闲,眼睛像是在看谁,又像是谁都没看,或许,在它来说,看与不看,它都知道,这些人来上里是做什么的。它走过我身边,朝我瞥了一眼,像是欢迎我,又像是同我打招呼。啾啾,一声鸟鸣,狗“噌”的一下蹿了过去,三步两步跑下河去。我循声望去,几只飞鸟在河岸盘旋,唔,原来,它是追逐水鸟嬉戏去了。
水旺的地方,必然桥多,而上里的桥乃是上里的一大特色,每一座桥都很古老,每一座桥都很沧桑,每一座桥都长满了绿绿的青苔,每一座桥都长满了我叫不上名的杂草,有枯死的,有新长的,衰老与新生并存,繁荣与陈旧相依,它们在没有土壤的桥上生,它们在没有土壤的桥上长,一茬一茬的新生与死去,便成了又一轮生命的起点。看着它们,我不禁感慨,时光不仅沧桑了容颜,也沧桑了岁月,一轮一轮的岁月,在时光中沉淀,最后沉淀成斑驳的光影,那些留下的,是往日岁月的履痕和见证。
朋友叫我,该走了,我应着,但脚下明显的有不舍,我在原地站定,回过头,将上里细细地环视了一圈,而后转身,走过之后,仍忍不住频频回头。我在内心想,要是时间允许,在此住上一晚,在古老的吊脚楼内,有两个人,分椅而坐,品着茶香,听着水声潺潺,伴着时时吹来的古风古韵,上里的夜晚一定是静谧安详而令人沉醉的。可是,我要走了,这个“假如”在此次不能实现,只有留待以后的时间,但能在时间仓促的情况下赶来上里,已让我没有遗憾,那么此次,暂且作别,或许,我会再来,在一个尚不确定的时间点,与上里来一次意外的重逢,留一份缺憾给自己,留一份遐想予未来,生活便有了另一种盼望和期待。
我步出上里,桥头依然有学生在全神贯注地作画。上里,是他们眼中的风景,而他们,又成了我们眼中的风景,他们与上里一起,构成了我记忆中的上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上里,静好!
愿时光依然……
(本文获“四川散文佳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