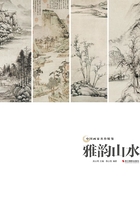
山水画史与文人
殷心悦
山水是中国画的一大画科,极得文人喜爱。文人务风雅、求神韵的审美,一直伴随着中国画的发展。早在南北朝,宗炳就提出: “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这种对山水画充满文人气息的审美,与同时代兴盛的山水田园诗可相互印证,如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山水画里投射了诸多情怀:寄目畅神,退居遣怀,山林之趣……
山水画起自何时,已不能细究。隋唐时,山水画已是独立画科,中原流行青绿山水,善为此道的有展子虔和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就是展氏作品,李昭道名下有《明皇幸蜀图》,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山石树木以细笔勾斫,敷以青绿重彩。而善水墨山水的吴道子、王维、张璪、项容,却没有可靠作品传世,画史所载《辋川图》《寒林图》等则是“水仙已乘鲤鱼去”。关于唐代水墨山水的只言片语并不能复原其大体面貌,我们也只能从韩休墓壁画山水屏风、贞顺皇后墓壁画六扇屏风等墓室壁画中寻找影子。毕竟隋唐时,佛道人物是最重要的画题,这一点从《历代名画记》《益州名画录》所评所载就可看出,占据绝大部分篇幅的是关于人物画的品评。
五代时,画坛南有董、巨,北有荆、关。董源供奉南唐宫廷,画史上说他: “善画山水,水墨类王维,著色如李思训。”今归在他名下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龙宿郊民图》,与其说是董源,不如说是董、巨传派的作品。僧巨然师承董源,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由南唐入宋,名下作品有《层岩丛树图》《秋山问道图》等。荆浩,博通经史,隐居于太行山中,宋人赞他:“范宽到老学未足,李成但得平远工。”名下《匡庐图》山峦层起,云烟飘拂,与画史所言“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相符。关仝,师承荆浩,喜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笔愈简而气愈壮,时人以“诗中渊明,琴中贺若”誉之。
北宋是山水画的一个高峰,宋人对此颇为自信,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称: “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经过唐末大乱后,朝廷休养生息,推行文治,完善科举制度,印刷术的推广则使接受教育的成本变低,下层文人有向上晋升的途径,完成了由贵族参政到平民参政的社会转型。安定的社会环境,自由的文化氛围,自然有利于绘画的发展。也是在这一时期,山水画成为重要画题。不少山水画画家是文士,且并不以售画为业,《画继》中记录了不少今已亡其作品真迹的画家,留下许多拒绝王公地位、不慕名利、以画自娱的美谈。

夏景山口待渡图·董源
宋初,李成、范宽、关仝被誉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李成,祖上是先唐宗室,以儒学传家,李成本人好读经史,不为荣进,善画雪景寒林,寒林代表作尚有《读碑窠石图》《茂林远岫图》,雪景已失传。范宽,始学李成,画千岩万壑如行山阴道中,名下《溪山行旅图》《临流独坐图》,均为高头大卷,气势恢宏,望之高山如在面前。郭熙、翟院深、许道宁、王诜等皆学李成。郭熙善画云烟出没,峰峦重叠之态,深受宋神宗喜爱,时宫中墙壁屏障多是郭熙所画,著有《林泉高志》,阐述自己对于山水的理解,其言“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这大概是所有文人画家的梦寐以求。许道宁晚变李成之法,画笔简快,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成一家。《渔父图》树石挺峭,山势起伏,群山林立,确与旁人迥异。除却学李成外,还有燕文贵、赵令穰、王希孟等。燕文贵不专师法,自成一家;赵令穰继僧惠崇,画汀渚水鸟、江湖小景;王希孟和赵伯驹、赵伯骕兄弟则延续青绿山水传统,运以宋人笔墨,使得《千里江山图》《江山秋色图》《万松金阙图》等图的面貌与唐人青绿截然不同,其中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又与他人不同,此画松树、丛林都呈扇形排列,极具装饰性。
董、巨之后,善画江南云山的还有米氏父子——米芾与米友仁,米芾已无作品存世,米友仁名下有《潇湘奇观图》《云山得意图》等,都是不拘绳墨,点滴烟云的随意之作。这种不加雕琢的审美趣味,正是米芾、苏轼所提倡的文人审美——“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云山墨戏图(局部)·米友仁
徽、钦二帝被虏,宋室南渡,定都杭州,与金人划江而治。虽只有半壁江山,皇室贵戚依旧延续了旧时传统,于西子湖畔经营园林,游幸湖山,宴饮享乐,诗歌相酬。杭州的自然风光使得南宋院体山水画呈现出与北宋截然不同的面貌,由崇山峻岭改为湖光山色。南宋画院从李唐到马远、夏圭、刘松年,所画山水多用斧劈皴,树石画法也更加简略老辣,平远小景,构图多在一边一侧,因而后世呼之以“马一角,夏半边”。这种宫廷小品画便于把玩,使得它与北宋巨轴长卷出现了不同的题诗的形式,现存北宋作品上几乎没有同时代人的题诗,而现存南宋小品画,有一些团扇画,皇帝和后妃在画作或对开上题诗,诗、书、画彼此相互映衬,这种只属于文人的风雅趣味,也使图画的含义得到扩充。
元代国祚不过百余年,但这百余年里人才辈出,前有赵孟 、钱选,后继者有王渊、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高克恭等。赵孟
、钱选,后继者有王渊、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高克恭等。赵孟 、钱选由宋入元,提倡“士气” “复古”,变革唐宋以来青绿山水的富贵气,以书入画,强调古拙的审美趣味。当然赵孟
、钱选由宋入元,提倡“士气” “复古”,变革唐宋以来青绿山水的富贵气,以书入画,强调古拙的审美趣味。当然赵孟 天资过人,对于山水名家都有学习,如《鹊华秋色图》就熔诸家于一炉,设色是青绿的,山石树木既有李、郭又有董、巨。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则继承了赵伯骕《万松金阙图》的装饰感。黄公望博通三教,旁晓诸艺,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晚年学画,师董源而自成一体,画雪景尤为奇绝,如《九峰雪霁图》山石参差错落,枯树凌风披雪,全无师承。倪瓒,号云林生,善画林木平远之景,也就是所谓的一水两岸,以侧锋虚笔画石,作画得“虚中实”真谛。吴镇,号梅花道人,山水师法巨然,而刚猛过之。王蒙是赵孟
天资过人,对于山水名家都有学习,如《鹊华秋色图》就熔诸家于一炉,设色是青绿的,山石树木既有李、郭又有董、巨。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则继承了赵伯骕《万松金阙图》的装饰感。黄公望博通三教,旁晓诸艺,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晚年学画,师董源而自成一体,画雪景尤为奇绝,如《九峰雪霁图》山石参差错落,枯树凌风披雪,全无师承。倪瓒,号云林生,善画林木平远之景,也就是所谓的一水两岸,以侧锋虚笔画石,作画得“虚中实”真谛。吴镇,号梅花道人,山水师法巨然,而刚猛过之。王蒙是赵孟 外孙,颇得家学,被倪云林赞为“王侯笔力能扛鼎”,山水构图大多繁密,草木葱茏,用笔略显琐碎。这些画家的文学造诣都极高,诗画相酬也是他们交往的一部分,画作大多有诗相配,不是自题就是友人题,如倪瓒赠友人的《安处斋图》,上有“湖上斋居处士家,淡烟疏柳望中赊。安时为善年年乐,处顺谋身事事佳。……”黄公望《九峰珠翠图》无黄款,友人杨维桢题“九珠峰翠接云间,无数人家住碧湾。老子嬉春三日醉,梦回疑对铁崖山”。至此,诗入画已是常态,绘画成为诗、书、画三者结合的艺术。此外,高克恭继承米家云山,唐棣、朱德润等人对于李郭画派颇为钟情。
外孙,颇得家学,被倪云林赞为“王侯笔力能扛鼎”,山水构图大多繁密,草木葱茏,用笔略显琐碎。这些画家的文学造诣都极高,诗画相酬也是他们交往的一部分,画作大多有诗相配,不是自题就是友人题,如倪瓒赠友人的《安处斋图》,上有“湖上斋居处士家,淡烟疏柳望中赊。安时为善年年乐,处顺谋身事事佳。……”黄公望《九峰珠翠图》无黄款,友人杨维桢题“九珠峰翠接云间,无数人家住碧湾。老子嬉春三日醉,梦回疑对铁崖山”。至此,诗入画已是常态,绘画成为诗、书、画三者结合的艺术。此外,高克恭继承米家云山,唐棣、朱德润等人对于李郭画派颇为钟情。
明清以来,文人画可谓达到全盛。而此时的山水多研习前人,王世贞对此总结得很好: “山水,大小李(李思训、李昭道)一变也;荆、关、董、巨(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范(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又一变也;大痴、黄鹤(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几变实在是很恰切的归类,道尽了明清山水的几大门派。

溪山行旅图·范宽
入明后,江南文士因多是张士诚旧部,不少遭遇重刑。明廷一开始采取了抑科举、增税赋的措施来打压江南大族,迫使他们不得不耕读传家,以求自保。沈周不科考、辞征召,正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一现实的反映。明代宫廷崇尚院体、浙派,戴进、李在、商喜等宫廷画家,既能画简笔狂放的马远夏圭一路,也能兼学范宽郭熙,对于职业画家来说,各家皆能是职业素养。而江南一带则继承前贤,学习倪、黄、吴、王。沈周的老师杜琼、刘钰都是学习王蒙、董源、巨然的高手,沈周早年亦是学习黄鹤山樵,《庐山高图》就是沈周早年学习王蒙的杰作。《庐山高图》是沈周为老师陈宽贺寿之作,既寓意寿如山不倾,又赞美老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图上高山巍峨,树木葱茏,流瀑飞溅,右上还题诗《庐山高》一首;晚年变法,博采诸家,对吴镇、黄公望的学习尤其明显,鼎鼎大名的《富春山居图》就曾是沈公藏品。沈周弟子众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文徵明、唐寅。文徵明粗笔一路从老师沈周来,老辣更胜之,细笔一路则多学赵孟 、王蒙。随着江南文人的出仕入阁,江南地区文化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恢复,画院画家亦是追随文、沈。文徵明子文嘉、族侄文伯仁都善画山水,弟子有周天球、陈淳等人,主要继承了文氏花鸟。晚明江南颇好倪、黄,江南士族以家藏倪、黄为傲,如顾正谊、董其昌、王时敏就痴迷收藏黄公望。在顾正谊的影响下,董其昌对于黄公望也用心颇多。董其昌对书画的体悟过人,下笔虚和,似无发力处,全从神会来。他对于山水的审美趣味,不仅影响同时代如陈继儒、莫是龙、赵左、李流芳、查士标、龚贤、八大等人,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的美术史写作,本书的框架也隐含在他这几句话中:
、王蒙。随着江南文人的出仕入阁,江南地区文化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恢复,画院画家亦是追随文、沈。文徵明子文嘉、族侄文伯仁都善画山水,弟子有周天球、陈淳等人,主要继承了文氏花鸟。晚明江南颇好倪、黄,江南士族以家藏倪、黄为傲,如顾正谊、董其昌、王时敏就痴迷收藏黄公望。在顾正谊的影响下,董其昌对于黄公望也用心颇多。董其昌对书画的体悟过人,下笔虚和,似无发力处,全从神会来。他对于山水的审美趣味,不仅影响同时代如陈继儒、莫是龙、赵左、李流芳、查士标、龚贤、八大等人,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的美术史写作,本书的框架也隐含在他这几句话中:

庐山高图·沈周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虽然董其昌讲“非吾曹当学”,这并不意味着董其昌不欣赏、不学习北派,他的《山水树石小稿》就有学习北派的痕迹。
明清鼎革,江南死伤惨烈,不少志士殉国,或落发为僧,或谢绝仕途。王时敏、王鉴明亡后居乡里以书画自娱,提携后进,王翚、王原祁亲得其指授,对南宗前贤锐意摹学。四王是清代山水大宗师,从江南到宫廷,都以四王为嫡派正宗。四人的仿黄作品尤为相似,其中王时敏苍茫、王鉴秀润、王原祁刚强、王翚清丽。四王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注重笔墨,师南宗不遗余力,只有王翚博采诸家,能画一些实景。四王追随者如黄鼎、唐岱、王学浩辈尚得四王之笔墨余绪,小四王(王昱、王愫、王玖、王宸)后已然江河日下,既无笔墨也无气韵可言。四僧是典型的遗民画家,八大、石涛、髡残、弘仁都是明亡后出家为僧的,四人的山水面貌也与众不同,但若因此以为他们的作品过分强调身世之感、亡国之痛,那就太过望文生义了。清初还有一些地方画派,如新安、金陵、扬州。新安画派有查士标、渐江、程正揆等人,他们大都以倪瓒为宗,笔墨较为纤细。金陵画派有龚贤、樊圻、邹喆等人,龚贤学习董、巨,以苔点画山水,其余诸人都延续了明代宫廷院画传统。扬州画派都是职业画家,多画花鸟,所谓“金脸(人物画)银花(花鸟画),要饭山水”,这固然是由于扬州一带盐商喜好花鸟,但山水难成难好也是事实。罗聘、李鱓、华嵒辈偶尔也画山水,其中李鱓画得最好。

山水花鸟册之六·八大山人

秋水鸬鹚图·齐白石
近代山水,有金城、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等,此外四王尚有余绪,如吴湖帆山水从四王。这些人中,齐白石自创山水,吴昌硕则以金石入画,而追摹前贤还能自立门户的唯有黄宾虹一人。黄宾虹在书画上造诣很深,注重笔墨,有“五笔七墨”论,对于画史也颇有研究。金城能画不同面貌的山水,张大千、傅抱石不重笔墨喜欢渲染,开现代山水之先河。
梳理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中国的山水画史几乎是一部文人史:诗书传家的读书人、有功名的举人秀才、有地位的官员……到了元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元四家都通经史,能诗词,并且都有很高的水准。文人画家对于绘画的追求不仅是表面的雅致,也注意深层的内涵,《尔雅注疏》: “雅者,正也。”天地运行是正,三纲五常是正,草木生发各有时节是正,五阴五阳是正,天地大道是正。我们评论一个事物为“雅”的时候,往往也隐含了“正”这层意思。什么是俗?不正就是俗。这与儒家追求的正道、正身相符。画家在绘画里构筑的是一个完美运行的世界,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山水画的不是人间实景,而是万物之理。这正是为什么以董其昌、王时敏、八大的高才大志,却不写生,一心模仿,他们真正要画的是天下至理,这又岂是写生可以做到的?

拟古人山水图之三·黄宾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