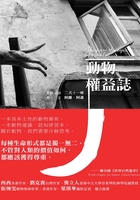
Part I -2
消失中的鄉郊生態
阿蕭
在那大片綠油油的農田、縱橫交錯的水道上,農夫正荷著鋤頭,為田地耙泥。農耕生活尚未被淹沒,偶爾,甚至可見農夫在驅使牛隻犁田。
新界牛在田裡,儘管只是踐踏泥地、在泥地打滾、咀嚼雜草,都為當地生態帶來好處。牠們降低了生長在淡水塘壆上的植物高度,吸引不同種類的水鳥棲息。在較矮的植物及水牛足印的水坑和沼澤地,會發現赤頸鴨、針尾鴨和蒼鷺等水鳥的蹤影,罕有的黑臉琵鷺、鳳頭麥雞,也受農地環境所吸引。
農業對本地生境保育起著作用,即使是棄耕的農地,也是鄉郊一個必然的構件。「沒有農地,就沒有鄉郊」,鄉郊是鄉村和郊野的結合體,英文「Rural」的語源說明了「開闊土地」之意。以新界東北發展範圍內的古洞為例,河上鄉及塱原一帶,是淡水濕田耕作為主的活躍農業區,近燕崗村一帶多為旱田耕作,塱原南面為天光甫,混集寮屋區及農地,是多樣化生境。
農業的生態多樣性
古洞位於上水西部,落馬洲的東南部,是附近雙魚河流經之地。河上鄉村是那裡比較為人熟悉的其中一個村落,居石侯公祠是村內的地標建築,更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村內還有洪聖古廟及排峰古廟等歷史建築。從河上鄉走過雙魚河的另一邊就是塱原濕地,那裡有不少農地還是用於耕作,各種各類的蔬菜田園盡現眼前,除了農作業,塱原濕地更是很多候鳥南飛過冬的棲息之處。
長春社與香港觀鳥學會,在2005年開始「塱原可持續發展計劃」,在當地以農業及生態保育結合的方式保育部分農地,藉水耕田耕種保育濕地生境;清理部分荒田、注水,使當地鳥類數量增加,令水鳥留下、禾花雀重臨,截至2012年7月,塱原共錄得286種雀鳥。
開闊的塱原農地,為一些偏好開闊地的鳥類如椋鳥、鴉類等,提供棲息空間。不同的農作物能提供不同的環境,例如通菜或西洋菜田,是不少雀鳥愛出沒的地方。通菜田有乾田和濕耕田,西洋菜田則是濕耕田,吸引牛背鷺和沙錐躲藏;鶺鴒和鷚則較偏好乾田。
從生物學角度看,雀鳥往往是食物鏈或食物網中最頂層的消費者,雀鳥多的地方,可推斷其食性層次以下的生物量亦會多。塱原有不少昆蟲,常見的有蝴蝶、蛾、蜻蜓、螞蟻,以及螻蛄(俗稱土狗)。蝴蝶的愛好者,常在當地驚見種種罕有品種,如黃鈎蛺蝶Polygonia c-aureum(Comma),有著橙色像水印般的花紋翅膀;雙子酣弄蝶Halpe porus(Dark Brown Ace),屬不常見的蝴蝶品種;柑橘鳳蝶Papilio xuthus(Swallowtail),牠翅膀形態優雅,飛行快速,喜歡訪花。除了昆蟲,在濕耕田和灌溉水道常有福壽螺,灌溉水道亦有魚類如塘虱和非洲鯽等。
農作物也是雀鳥的小生境。生長得較茂密的植物,自成一個庇護所讓雀鳥躲藏。一些雀鳥亦會啄食農作物的種子、花、果或嫩葉。食用的植物集中種植,吸引大量昆蟲到來,間接吸引以捕食昆蟲維生的雀鳥。近燕崗村的荷花池,經常吸引偏好開闊淺水生境的林鷸和沙錐棲息。在夏季荷花生長得茂盛時,可發現有彩鷸在荷花池內哺育幼鳥,因荷花寬闊的花瓣和葉子,提供了掩護,讓幼鳥躲藏起來。
2008至2009年間,政府委託研究顧問公司在當地進行全面生態調查,結果顯示,塱原有多種濕地生境,包括仍在耕種及閒置的水田及旱田、池塘、沼澤、緩衝河流及綠化堤等,這些生境使塱原形成了一個豐富的生態系統。
高爾夫球場耗盡土地自然資源
農業關乎食物自給自足和糧食安全,亦同被喻為生態保育的重要手段。在開拓土地以作發展時,盡量避開農地,是政府應有之義。然而,在新界東北發展的三個地區當中,預計約有98公頃農地將會消失,而這土地面積,足有五個維多利亞公園般大。凝望古洞南面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它雖同樣是大片綠油油的草地,但其生態價值遠遠比農地為低。在政府2008年的「更新陸上棲息地保育價值評級」報告中,列明農地/耕地屬高生態價值生境;而高爾夫球場則屬生態價值生境,跟禿岩或禿土、人工改道河溪、人工岩岸/硬岸、石礦場同級。
高爾夫球場的耗水量極高,同時也是個生態破壞者。高爾夫球場單一的種植,形成單一的生態系統;而為了維持高爾夫球場的人工草坪,保持一定高度,經營者噴灑施放大量殺蟲劑、滅菌劑、化肥等,例如麥草畏、百菌清等。曾統計,這些農藥多達五十種,不但使球場土壤帶毒,而且經澆水或降雨,又隨水滲透到地下或流入河渠。鳥類等野生動物食用了聚毒的植物或昆蟲,毒素積累在體內,可能導致其後代夭折。
回溯高爾夫球場的起源,它是來自英國蘇格蘭的高山牧場,當地崎嶇貧瘠但牧草豐茂,牧人們用驅羊杖擊石自娛自樂,後發展為體育活動。由於當地地處濕潤的溫帶海洋性氣候,每年上千毫米的降水和濃霧,牧草任由人踩畜啃,都不必用上化肥農藥,十分茂盛。然而,香港的地理氣候與蘇格蘭不相同,營造綠油油草地必須人工化,干擾了原有自然生態系統,貶抑鄉郊的生態價值,使港人為虛耗土地和自然資源付上沉重代價。
地皮屬政府所擁有的古洞南的高爾夫球場,面積達170公頃,約一個荃灣般大,若土地以中密度發展,預計可容納十萬人口。反之,現時球會登記會員達數千,非會員的大多數市民,卻無法進內使用空間。偌大的土地,生態價值低之餘,其使用率之低亦可見一斑。
不過,政府未有把高爾夫球場收回以作發展的規劃用地。至2013年7月,東北發展計劃的方案內,反而擬定將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三區、涉及787公頃土地列作發展用途,其中115公頃作住宅用地。規劃中,受影響的人口卻達數千戶、過萬人口,無數家園和社區鄰里關係的活動將面臨瓦解;而發展亦會令香港損失98公頃農地,其影響之深遠,並非一個高爾夫球場的廢存所能比擬。
土地是人們安身立命、紮根繁衍之所;在以耕住合一的鄉郊裡,沒有農地就沒有家,農夫沒有謀生本錢,也沒法種出新鮮甜美、瓜爽肉厚的蔬菜,讓本地維持一定自給率;沒有農地,亦使無數生物物種失去棲地,無處容身。
土地倫理觀
在香港,有四成土地被劃作郊野用地,當中約一成未受《郊野公園條例》保護,大部分屬私人農地,不能加蓋建築物;亦有像塱原般具生態價值的保育地區,同樣不能改變用途。人們能在農地和鄉郊得以大興土木,生態價值是一個關鍵因素。隨漁農業式微,擁有業權的村民無發展農地的權利,但荒廢卻有可能帶來「機遇」。在鄉郊,常見到不少地方給傾倒泥頭,有人擅把農地改為停車場、廢車場,甚至建築廢料堆填區,試圖藉此減低土地的生態價值,以企圖更改土地用途。
此外,政府亦推出「新自然保育政策」,選出一些具較高保育價值的地點,包括沙螺洞、大蠔、鳳園、鹿頸沼澤和深涌等,並推行放寬土地發展限制的「公私營界別合作」,讓土地擁有人可以提出合乎保育條件的發展計劃,即是改變附近農地和保育區的土地用途,更有說,發展商過去二十至三十年購得的農地「存貨」問題,從而得到「解決」。
縱觀本地的發展機制和邏輯,土地的生態價值雖是一個關鍵,卻是非必然的考慮因素。在生態價值受到重視或漠視的過程中,也許源於沒有將土地倫理中的「生物群落」概念納入發展的考量中。一般關於土地倫理的討論,李奧波(Aldo Leopold)在1949年《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一書中發表的「土地倫理」概念中指出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如果是促進生物社群的整體性(Integrity)、穩定性(Stability)以及美麗(Beauty),就是正確的;反之,則是錯誤的。」
李奧波的土地倫理認為,人與其他的動植物、岩石、土壤、水等的成員共同組成一個生命共同體(Life community)或土地共同體(Land community)。作為這個土地共同體的一員,人們有道德上的義務來維護整個社群的長期利益,亦即人、動植物、岩石、土壤、水連成一個整體社群,必須維持著健全的土地生態系統,保障群落的整體利益。
「生物群落」以「土地金字塔」的概念來說明。「土地金字塔」就是藉由太陽的能量在生物與非生物之間流動,所串連而組織起來的結構。土地不只是土地,是流過土壤、植物及動物循環的一種能量泉源,食物鏈是引導能量向上的活管道;也是由個別的動植物所構成的,死亡及腐化則將它轉回到土壤,形成一個持續的生命循環。而造成物種突然滅絕的活動,如開發土地帶來污染,則會封閉一些食物鏈管道,破壞土地生態系統。
在保育和發展的權衡輕重上,若把倫理的觀念擴展到人與土地的關係,生態價值是個重要指標,平衡著「生物群落」的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