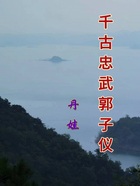
第14章 相见难相识
公元757年12月
唐廷两位天子携手同返长安,消息不胫而走。此时的唐土百姓历经战祸已是整两年,无数人家房宇荡尽,妻离子散,被掳遭害,血沃千里,惨状不忍目睹。真是:故园山河依旧在,城池黎民半数亡。活着多是从刀口枪尖上挣脱了性命的,整日为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而长泪不干。原以为再无天日可见,忽闻叛胡败溃,国祚已复,干戈将平,归乡可望,哪有个不喜极涕零。
然而北边范阳城里却是日益惶乱不安。尤其节度使官衙内外,恰似暴风雨前蚂蚁窝,出出进进应召前来的将军谋士,探马斥候,带来各路消息千头万绪,真真假假。这里上至大将军史思明,下至街头贩夫走卒,自十月得知唐军已取洛阳,燕皇安庆绪逃亡,都有一个疑惧:唐军何时攻打范阳?
如今两个月过去,不见唐军动静,却在个把月前来了场虚惊。那日范阳南城外,突见万余兵马直扑而来,惊得守城军士慌忙紧闭城门,飞报大将军。待史府长子史朝义受父命登上城楼时,那人马已围聚城下。
莫不是太原老对头李光弼打来了?朝义心头大惊。但见城下军容混乱,旌旗残破,兵士多半丢盔弃甲,疲惫不堪,怎么看也不像是那位军纪肃正,号令严明,最善御兵之唐廷名将部下。直到看见一面“李”字大旗勉强撑在队伍之前,又见旗下有位战袍染血的将领高喊“史小将军”,并报上自家姓名,言道兵败来投史大将军,方看清是安军悍将之一,李归仁。
朝义急报父亲。史思明狐疑,恐是安庆绪派来抢地盘。半晌后,方率几千精兵出城,以安抚之名,将万名安兵缴械,引至城外一处废兵营歇息食宿,只将李归仁及几员部将迎入城中官衙,暂为安置,并共议应对即将来攻之朝廷大军。
只是左等右等,不见唐军踪影。后有斥候来报,唐廷大军已班师回朝。那副元帅郭子仪受命驻守京师,颁榜城内外旅馆驿栈,严禁留宿可疑者,并派军士随时查看,全无发兵北上之迹象。范阳于是稍安。
此时,节度使府衙内有判官耿仁智为首几位心腹老吏,一直心向朝廷,此时再次劝说史思明:不如就此请降朝廷,总比被打降可得更多回旋余地。看来朝廷也愿早息战事,应会赦免将军胁从之罪。或以辖下州府为献奏请免死铁券,抑或官留原职也未可知。思明听了只说一时难决,再等时机。
府内却有三人听说王师大败安庆绪,中原已定,便再坐不住。其中一人尤为心急如焚。
那日,史府大娘子辛氏的侄女辛柳又溜进西院。见安玉丹兄妹正在院中悄声说话,连招呼也顾不得,急忙走过去道:“打搅。今有急事要同玉妹讨个商量。也请武兄拿些主意,不免唐突了。”
玉丹道:“不妨,请讲。”
辛柳虽知院里别无他人,仍左顾右盼后方压低声音问道:“妹子可知唐廷已然收复两京,二帝同返金銮?”
玉丹故作不在意,道:“满城已传得沸沸扬扬,岂有不知。”
辛柳又急问:“天下可是从此太平?”
玉丹不知其意,只道:“想必如此。”
辛柳长舒一口气,展颜道:“姐这几日也如是想。既然天下已归太平,便是时候去寻安太清。虽是已隔经年,不怕他相见不相识。在此处寄人篱下,断非长久之计。何况那史朝清……”说着眼中含泪,低下头去。
玉丹见状,想起曾听她说过,那位乳名豺奴的史家二郎人如其名,对猎艳女色果是如豺似狼。不到二十岁年纪,已有一妻一妾,在花街柳巷的相好也不知几多。更有甚者,但凡听闻父亲属下谁家妻女颇有颜色,必要设法到手。有人惧怕其父淫威暴虐,敢怒不敢言,也有为求升迁,甘献妻女者,让他越发肆无忌惮。眼见堂妹辛柳娇俏秀美,更是馋涎欲滴,几番言语调戏。只碍于母亲之面,尚未敢造次。但每每相遇之时,那双淫光逼人的鹞眼,足令辛柳心惊肉跳,整日难安。
此时玉丹问道:“安军已被击溃,四散奔逃,去向无定,辛姐将去哪里寻找?”
辛柳道:“昨日听姑父与姑母言说,那安庆绪自洛阳败逃,一路只剩疲卒千人,散骑数百,再有便是其弟安庆和等,及小将安太清。只因安阳邺城尚在安军将士镇守,欲投彼处。不想途中被太原唐将李光弼阻击,几遭灭顶。后来不知怎得一奇毒之计,反将李光弼及赶来增援的王思礼打得大败,败军方得逃进邺城去。想来太清此时必在那里。”
安玉丹本来久未听闻“李光弼”三字,自以为早已忘却。此刻忽闻那人之名,却似重锤敲击心鼓,一时咚咚跳个不停,热血直冲脑顶。待竭力沉静下来,方问道:“此话当真?”那声音竟是暗哑颤抖,不似自己。
辛柳摸不着头脑,问:“哪句话?”
玉丹不觉红了脸,道:“李光弼果真被贼击败?可曾负伤?”
辛柳略为回想,道:“姑父也是听逃来之安军所言,不知真伪。只是燕皇一行现在邺城,确为实情。”说罢,好奇地望着玉丹,问道,“玉妹与那李光弼相识?”
听她这样问,玉丹越发心虚,只得掩饰道:“他曾是先父帐下爱将,颇得言传身教,又足智多谋,善出奇制胜。适才听辛姐言道,他反被安庆绪以奇谋击败,故而诧异。”
辛柳闻听又道:“姐有一问,藏在心中多时,不知若是问起来,妹子可会嗔怪于我?”
玉丹以为她看透心思,又觉心如撞鹿,只得勉强笑道:“但问无妨。”
辛柳压低声音道:“我曾听闻尊先父乃是被唐朝皇帝冤枉赐死。此杀父之仇大于天。可这些日子以来,常与妹倾谈,却未曾听得你对唐廷怀一丝恨意,倒是时常打听王师战绩,这是为何?”见玉丹和武昭拓皆面露惊疑,忙道,“你们权且放心,我从未对他人言及。”
玉丹沉吟片刻,道:“先父确为唐廷所杀,然实乃死于哥舒翰之公报私仇。叔父安禄山反叛之前,曾游说先父附之。但先父嫉恶如仇,严词拒绝,并向皇上谏言禄山欲反,须严防之。那哥舒翰后来为朝廷启用,委以平叛重任。因其与先父积怨多年,便乘机诬告我父通叛,逼唐皇赐死。也是那时情势危急,叛我难辨,朝廷不得不‘宁可错杀,不留后患’。记得先父自尽前尤对我姐妹言道,‘历朝历代不乏冤死忠臣,既使蒙冤受害,亦不可叛国悖君,否则怎为忠臣。’先父既是为忠君而亡,为子女者,岂可悖父志而记恨朝廷。如今唐廷复兴,是非曲直终可甄别清楚。更有我义父郭子仪,一向敬重先父,如今执掌兵权,定会奏请朝廷为他平冤昭雪。”
辛柳听得出神,不觉忘记来此目的,又问:“安禄山反唐,自立大燕,玉妹既是忠臣之后,为何倒去投他?”
玉丹瞬间愣住,张口结舌,一旁武昭拓沉静答道:“纯是鬼使神差也。”
辛柳半信半疑,又问:“那李光弼……”
不等玉丹再为难,昭拓立即打断她道:“辛妹才说要去寻那安太清,又不知其行踪,却是何苦。或许不久他便自来投奔你姑父,如那败将李归仁。”
此时玉丹已复平静,心知问不出李光弼消息,也道:“你姑父不是早有归顺朝廷之意,乃识时务之人。如今燕军已是大败,一旦范阳归降,天下大治,安太清必来寻你。那时你却在寻他路上,岂不两下错过?倒是一动不如一静,在此等他还妥当些。”
辛柳默然片刻,摇头道:“此事我也想过。一来姑父言谈中,深恨安庆绪弑父篡位,必不相容。二来史府绝非我久留之地,那史朝清……委实不堪。”
玉丹听得懂她话中含义,便道:“敢是辛姐主意已定?”
辛柳点头道:“我此去寻他,也为劝其在不得已时,宁降唐,勿投史。”
“为何?”安、武二人同声问。
“我姑父早有心吞并安军,以壮范阳,进而取代之。”
玉丹又是一惊,忙问:“史大将军不是已是有心归唐么?”
辛柳冷笑一声,道:“姐我虽不问国事,但姑父母他们议谈并不避我,曾说朝廷不会真心纳降,必得本部实力壮大到朝廷不敢轻动,方可安心。故不停聚降纳叛,招兵买马,集粮造械。我只恐这些风声传出,朝廷疑心,派大军来讨。我若不早早离了这里,怕到头也要玉石俱焚。”
玉丹没想到,这位看似柔弱娴静的女子竟有此眼界,心中暗赞,只问道:“辛姐果真要一人上路?”
辛柳道:“我有个自小服侍的乳娘,四十余岁,健壮精敏,说是要将我作男子装裹,扮作母子同行。只是惧怕姑母发觉我失踪,派人追寻。”
玉丹道:“那也容易。你在房中给她留下一信,只道是怕唐军攻打范阳时,给他们添累赘,自己先与乳娘奔乡下躲避去了。想她便无意追究。”
辛柳连声称好,又问两人:“你们兄妹还要留在此地?”
玉丹敷衍道:“姐来之前,正与武兄商议着,不必挂心。姐要一路保重,后会有期。”
辛柳于是与二人依依道别。她这一去,竟是经历了一年多艰难。其间与心上人安太清几番错过,在此暂且按下不表。
辛柳走后,武昭拓见安玉丹颇为心绪不定,便猜到是因为骤闻李光弼战败而忧心。在灵武时,他从郭府家人议论中已听闻那员朔方名将拒婚之事。玉丹从来对此事绝口不提。他以为时过境迁,早已忘怀,此时方知这位看似寡情少爱的女子,实乃一往情深而不自知。
他默然长叹,片刻方试探道:“方才玉妹与我商议,言道既然王师已定中原,再留范阳无益,不如各奔前程。为兄也有此意。妹既欲往岭南寻母亲家人,我便自去灵武见义父义母,再回故国打探。若再无他顾,何不就此准备上路?”
安玉丹神情犹豫,望着他心不在焉勉强微笑道:“兄长此去,肩负石国重任,请自先行。愚妹还有些许琐事要办,便不与兄同行。见着郭府义父母,代妹多多致意。”
昭拓心中明白,怅然点头,自回房收拾。不一刻带着行囊出来,见玉丹仍怔怔地立在院中发呆,便走过去,从怀中摸出一物,轻轻放到她手中,柔声道:“这原是我用重金聘请有名工匠,为小妹金丝凯娅公主特制的嫁妆,还未及送她,便遭那高仙芝屠城劫掠。如今再用不上,就此送与你,也是为兄对玉妹的殷切祝祷,惟愿所托良人。不知何人有幸,能得贤妹忠孝之德行相辅,应是世间最有福分之人。”
安玉丹只觉手中之物沉甸甸,定睛一看,是个手掌大小锦帕包裹。帕子白底绣花,用绛紫、宝蓝、金黄、绯红、碧绿各色丝线绣成金孔雀,饰以飘逸彩云纹饰,满是西域之灵动华丽。她小心揭开锦帕,立时大吃一惊。原来帕中包着是只繁华炫目的金镶玉手镯。尽管她自己从不戴钗环戒镯,倒也见过价值千金的宝玉明珠,金钏螺钿。可手中这只精制手镯,却非金钱可以估价,眼见得是浓情深意之凝集:羊脂般细腻的玉环纯白无暇,环身镶有众星绕月五朵镂空金花,花心嵌着五彩宝石,皆绕以莹润珍珠,那般雍容华贵,岂是世间寻常首饰。休说佩戴,单是捧在手里,已见溢彩流光,夺人心魄。
玉丹惊讶之后,忙将玉镯用锦帕重又包好,递给昭拓,道:“如此显贵之物,妹子断不能收,必奉还兄长。”
昭拓不接,口中道:“此锦帕是凯娅妹妹亲手绣制送我,此玉镯是我亲自设制,并监工镶成。此二物即是我兄妹当年亲情盛载。如今我与小妹已是天人永诀,再留身边,也是枉费思念,也不妥贴。妹若嫌弃,便只当为我暂存,异日相见,再送还于我,可好?”
听石国王子如是说,玉丹只好将锦帕玉镯贴身收起,道:“兄长放心,来日定当完璧归赵。此番回到郭府,宜速向义父表明复国心愿,请代奏皇帝,赐封你为国王,即可名正言顺早成王业。”
昭拓道:“但愿如妹所言。为兄早已想过,朝廷助我,运也;朝廷无视,命也。然解救石国之王室与百姓出水火屈辱,却是天意。我将以天意为己任,直到与父王、母后及兄弟姐妹相见于天国!”
听他这番泣血剖心之悲壮言语,安玉丹忽觉眼前这矮小黧黑的西域王子竟似巨人般凛然伟岸,雄健正直。正待再说几句,只见他已背着行囊,转身朝院门走去。临出门之前,又听他头也不回道:“玉妹勿忘,石国有位兄长可以投靠!”
院门在其身后砰然关闭,遮断玉丹视线,令她蓦然惆怅。几个月朝夕相处已成习惯,此时方觉亲情渐生,却已到了分手之时。
她在院中独立少顷,拿定主意先去太原看个究竟,再作打算。于是回房,巡视一番,只包起那身从灵武带来的玄甲军皂绢铠胄及些许碎银,便直奔府苑西门。与相熟的门卫军士打过招呼,又去马厩牵了那匹黄彪马走上上大街,却不想迎面碰上史朝义。自从住进史府,她从未与这史家大郎交谈,此时正要低头错开,却被他挡住去路。
见安玉丹仍是男子装扮,又行色匆匆,朝义上前一步,问道:“敢问安家小郎,要去何处?”
玉丹只愣了一下,就扬起脸,冷冷道:“有劳史将军动问。但不知何时起,在下外出须向将军报备?”
朝义笑了笑,道:“非也。某适才见安小郎的义兄策马出城,眼前又见小郎牵马而来,不觉好奇而已,请勿以为意。”
玉丹这才放下心来,又听他言语温和,只得诳语应答道:“义兄与在下拌了几句嘴,赌气走了,正要去将他劝回。”
朝义道:“速去速回,莫等城门落了栓。”
玉丹不再答话,竟自上马而去。
两日后,太原留守府衙门前守卫军士挡住一位清俊少年。只见他一身陈旧玄甲军甲胄,头盔上的护项布巾紧包住下巴,只露一张俊脸,口中嚷道,有要事求见李大将军。问他有何事,少年只说必得面见大将军,方能相告。军士正拿不定主意是否进去通报,只听一阵沉雄步履,就见里面有几位魁梧威严的将军朝大门外走来。
少年看准其中一位凛然傲岸,目光冰冷的人,忙甩开门卫,抢步上前道:“李将军,在下……”
那人正是河东节度使兼北都太原留守,李光弼。他只瞟了少年一眼,不听说完,便一把推开,朝一名亲兵校尉牵来的骏马大步走去。那校尉短小清瘦,看上去十分年轻,目光却异样精敏,牵的那匹高头军马对他温顺服帖。众部将快步跟上。那少年追过去,望着光弼背后高声道:“在下来自范阳节度府,有要事相告!”
此话一出,就像沙场士兵听得鸣金号令,众人一齐收住脚步,转过身紧盯住少年。那个亲兵校尉拔刀向他走来,被光弼一声“张佑且退下!”喝住,又命少年近前,厉声道:“将方才之言再与我讲来!”
少年目不转睛望着他,一时面红耳赤,声音微颤,道:“在下原是朔方灵武城一读书人,为逃兵祸反被抓到范阳。因颇识数计,派在府衙通判耿仁智手下听换,作了一名吏目……”
旁边一将听得不耐烦,斥道:“谁听你闲扯,只将要事讲来!”
光弼朝那部将摆手,问少年道:“既在贼营做事,怎敢到此见我?”
少年尽力稳住心旌,道:“只因听闻耿判官及信都太守乌承恩等史思明亲近心腹得知王师已复两京,便力劝史某归顺朝廷。”
光弼冷笑一声,问:“倒要听那史贼怎讲?”
少年道:“这便是在下冒死前来,求见大将军之故。史某惟恐朝廷不肯恕其从叛之罪,尚在犹豫间。若大将军能奏请皇帝下诏安抚,许赦其罪,彼必归降。于是不劳王师,不伤将士,天下平定矣。”
光弼又是一声冷笑,道:“史贼乃叛党主犯,怎说是从叛之罪。必歼之以绝后患!”
另一部将接道:“大将军不必与小子多言。圣旨召吾等速去京师,不可延误。”
李光弼点头,转身上马。忽又回头端详少年,道:“某似曾与你见过,你是灵武何府小郎君,叫甚名字?”
少年闻听,似乎有些畏寒,紧了紧护腮布巾,拱手道:“在下安玉,不过一介贫寒书生,怎会有幸得见大将军。惭愧。”
李光弼复又看他,道:“某见你年少却颇有胆识,可愿为某仍在史贼大营走动,时传消息,也是你为朝廷效力,洗脱为贼所用之耻。”
少年略为迟疑,道:“愿为大将军效犬马之劳。”
8.
光弼朝他微微一笑,道声“甚好”,便与众将绝尘而去。可就这不经意一抹笑意,却令少年看呆了,立在原地,动弹不得。
读到此处,列位看官定然猜到,这少年便是男装安玉丹。
古有情圣言道:男子越冷漠,女子越倾心。这一场相见不相识,令玉丹五味杂陈。虽然人已去远,但她已清晰认出他那顶凤翅兜鍪上飒飒飘摇的红亮盔缨,还有他颈下牢系的丝织绦带,都是当年她亲手装点。那时节,得知父亲有意将她许配心仪已久的青年将军李光弼,又特意命人打制了这顶凤翅头盔,暗托郭子仪送与未来爱婿,她便含羞带喜,急忙将亲手编成的缨饰及绦带装点上去。谁知后来婚事不谐,令她心碎。看来他并不知道是她在那盔上倾注了一腔柔情蜜意,至今仍戴头上,此时却怎不令她睹物伤情,心绪难平。
就有路过之人为这呆立美少年驻足,“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玉丹发觉路人异样眼神,猛然清醒,心中暗道:“想我安玉丹自诩巾帼须眉,怎的今日竟如小儿女一般伤情悲怀?只见他体健无恙,也不枉来一遭。方才他要我传送史营消息,也罢,只当是为我义父效力,不是为他。”
想到此,她一把抹去眼中泪水,飞身上马,沿原路奔范阳而去。不料她此番鬼使神差返回史营后,又作出一番震惊天地之事,却仍是名不见经传,倒引发千年疑云。暂且不表。
*********
三日之后,长安晴空丽日,乍寒还暖。大明宫正南丹凤楼上,李亨着冕旒龙袍,端升御座。王室及朝中一、二品公侯分列两行,正三品以上文武百官静列其后。楼下是在京的从三品以下官员,依文武分列成行,京城卫戍军兵将围观百姓隔阻于圈外。
只听得楼上大宦官殿中监李辅国一声“捧旨”,一队身着镶铜华丽绢甲的仪兵从仪门鱼贯而出。中间一神武将军身高八尺,相貌俊朗,巍巍然双手高托捧旨玉碟。碟上十轴圣旨,严整叠成“山”字型,玉轴莹莹发光。随之,宫中大乐《功成庆善》蔚然奏响。金钟伴笙笳悠扬,羯鼓并玉螺激荡,好一派气吞山河,磅礴阔壮。城楼上下官民屏息静听,无不动容。
宏曲奏罢,只见禁卫三军将军鱼朝恩出列,双手从捧旨将军王强林所托玉盘中捧出顶上那轴,启御封,揽玉轴,展彩锦,朗声开读。百官肃然而立,静穆恭听。
“诏曰,自戡乱以来,朕之长子广平王俶,临危受命,拜兵马大元帅,领王师荡涤逆胡,敢当天地,指麾有度,速收二京,克复宗庙,残丑鼠窜。于戏,俶威震四疆,功宣华夏,宜册立楚王。钦哉,至德二年十二月。”读罢,端放回盘,又接着一一捧读。
“兵马副元帅郭子仪,乃风云有感,星象降生,兼文武之姿,识度宏远,谋略冲深,故能扫清强寇,收复二京,折冲千里,建兹大勋,成我王业。于戏,宜加司徒,兼兵部尚书,及同平章事(位同宰相),册封代国公。钦哉,至德二年十二月。”
“河东节度使兼太原留守李光弼,披荆棘而有功,历险艰而无易,仗其深略,为我长城,挫群凶之锐,全百胜之师,为庙堂之宝臣,成军国之重任,无愧前贤。于戏,宜加司空,兼户部尚书及同平章事,册封魏国公。钦哉,至德二年十二月。”
“朔方军兵马使仆固怀恩,平叛数战,出生入死,勇冠全军,屡建奇功。其族系满门忠烈,数十人战死国难,为取回鹘援军,送爱女和亲。于戏,宜拜左仆射,册封丰国公。钦哉,至德二年十二月。”
“北庭行营节度使,骠骑大将军李嗣业,植操沉厚,秉心忠烈,奉命勤王,征讨羯胡,每逢大战,必身先士卒,亲当矢石,频立勋庸,壮节可嘉。于戏,宜加任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卫尉卿,册封虢国公。钦哉,至德二年十二月。”
“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骁勇果断,知兵法,善谋略,立军严整,退不避罪,戡乱竭力,无不摧靡。于戏,宜加御史大夫,并司空,册封霍国公。钦哉,至德二年十二月。”
“限开元及蜀都、灵武之元从功臣,有守土没死王事者,并加伏赠。死节之士如颜杲卿、张巡、李憕及卢奕等各州郡主官皆加赠,并赐子孙官爵。战亡之家,免两年赋役。然哥舒翰、程千里等未殉节战场,乃于胡叛狱中受辱致死,不得褒奖。”
鱼朝恩捧出最后一份圣旨宣读:“朕之良娣张氏,皇族后裔,位尊身荣。朕昔在储贰,常得侍从,孕得朕二子,为皇室延绵后嗣。适逢逆乱,知难相随,辅助良多,望气如归,当能见节。于戏,宜册为四妃之一,淑妃。其所生第十二男佋,封兴王,第十五男侗,封定王,另有朕之未得王爵七幼子,皆同日封王。钦哉,至德二年十二月。”
一时宣读完毕,受封诰命大员一一稽拜领旨,叩谢皇恩。宫乐再度奏起,丹凤楼上下百官拜舞,山呼万岁。四周百姓皆手舞足蹈,喜形于色,以为从此治世明君再降,开元盛世重兴。
次日,李光弼领河东众部将,造访郭子仪朔方军驻城东营地大帐。见李嗣业已在那里,三人把臂言欢。
子仪命亲兵看座,光弼上前抱拳施礼道:“在下已知郭帅在圣上御前力陈弼之微功,特来拜谢。”
子仪紧握其手,道:“某不敢独贪天下之功。君率河东军掣肘范阳贼众近一年,王师方得游刃有余,故君之功不在某之下。再者,某昨日已将元帅兵符交还圣上,如今还是称某郭公为宜。”
光弼闻听一惊,忙问道:“圣上撤收公之兵权耶?”
子仪微笑摇头道:“并非圣上撤收,乃某自行交还。”
光弼越发不解,略为思忖,又问:“公惧‘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耶?”
子仪正色道:“此番安史作乱,只因藩镇坐拥重兵,骄狂自大所至。故圣上忧惧之心一时难消。今中原大定,某为安抚圣心,自释兵权矣。”
光弼闻之,默然片刻,方道:“然则贼酋史思明仍狼据幽燕广土,蠢蠢欲动。公大捷之后,当防轻敌也。”
11.
子仪点头,道:“某非轻敌。因得报,史思明经心腹将领力劝,如原信都(河北邢台西南)太守乌承恩等,欲弃安庆绪而归顺朝廷。又前者贼燕朝之伪相严庄,已获圣上所赐免死铁券。附叛州郡闻之,皆思归顺。日前已有伪燕之河北青州节度使能元皓,率全州人马来降。并有德州(山东)伪刺史王暕,贝州(河北故城西)伪刺史宇文德致信朝廷,上表弃暗投明之意。陷区多地亦有秘议复归者。如此算来,叛军之势已去十之八九,某有何故仍握王师兵符也。”
李嗣业插言道:“某也听闻,范阳已来人与朝廷联络,欲讨降后免死铁券。”
河东部将荔非元礼对主将道:“记得前日那范阳小郎君,也曾对大将军言及史某有思降之意。”
光弼闻众人之言,越发浓眉紧锁,道:“某与史贼交手经年,深知其阴险诡诈,包藏祸心,一似狡兽猛禽,若不根除,恐生不测。郭公万不可因疲战而懈怠也。”
话音未落,只听帐外有人高声道:“何人在此放肆,胆敢教训郭老爹!“
河东众将皆惊,齐齐转头望去。只见仆固怀恩虎步熊姿走进大帐,不管有人怒目相视,对李光弼道:”我家令公可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朔方上下,无不枕戈待旦,闻风而起。那叛胡摄于我军神威,早已丧胆,情愿来降。李将军一味危言耸听,莫不是怕失了平叛头功?“
李光弼闻之,怒形于色。荔非元礼等也奋袂而起,拔剑出鞘。李嗣业见状忙站起身,握住怀恩手臂道:”丰国公慎言,莫伤了与魏国公和气。“
郭子仪也严词道:“虢国公所言极是。我等如今皆朝廷倚重大臣,只可同心协力,共保社稷苍生,断无猜忌相伤之理。怀恩还不与李将军赔罪?”
怀恩闻听,只得草草向光弼抱了抱拳,口中道了一声:“得罪!”
光弼示意众将收剑,遏住恼怒道:“某且相忍为国!”
此时只听帐外卫兵通报:“禁军鱼朝恩将军到!”
未等众将起身相迎,那宦官将军已大步走进来,手中捧着一个手掌大黑檀木匣,直到帅案之前,将木匣端放其上。
众人不知此为何物,皆聚睛木匣。只有郭子仪认识,脸上顿现惊讶,站起身问:“我已将兵符奉还圣上,鱼将军这是何意?”
鱼朝恩不紧不慢道:“圣上口谕:残胡尚未除尽,王师兵符仍由兵部尚书郭子仪掌管。”说着,轻启匣盖,双手捧出一铜质鱼符,举到子仪面前,又道,:“请郭司徒验收。”
闻听这小小铜鱼竟身系朝廷大军调动,一众军头聚首打量。只见那兵符乃半爿鱼身,剖面有凸起错金铭文,清晰可见是六个铸字:天下兵马之符。
只听子仪道:“圣上隆幸,为臣感念不尽。然近期并无用兵之需,还要烦请鱼将军仍将兵符呈还圣上。”
鱼朝恩一愣,很快将手中兵符举得更高,声色俱厉道:“既知是皇上隆恩,郭将军请即刻收受兵符!”
子仪双手接过鱼符,仔细放回黑檀匣,严密盖合,又捧到鱼朝恩面前,语气恳切而坚定,道:“烦请鱼将军奉还圣上。”
眼见子仪坚辞不受,鱼朝恩不由得心中暗惊。又见帐中众目睽睽,心知不可将兵符强行留下,只得捧定匣子,提高嗓声道:“郭司徒拒受兵符。若是圣上怪罪下来,诸位将军须得给鱼某做个见证。”言罢,便愤愤往外走。
众将无人应承,见宦官出帐,相视大笑。这一班百战之将,历来杀人如麻,饮血止渴,见过无数惊魂阵仗,却不知这宦官厉害。只有李光弼撇见白脸宦官那双斜视三角眼中隐隐闪闪,捉摸不定的阴毒,暗吃一惊,替子仪担心,却又不便说出。
但无人知晓这回送兵符之事,竟是这鱼朝恩捣鬼。
就在昨日丹凤楼宣读圣旨之时,这宦官念着他人的道道封赏,心中嫉妒如虫噬咬,切齿怀恨想:“彼等武人,多凭父荫得官,偏又封爵拜相,光宗耀祖。想我鱼朝恩虽无家世,却人才魁岸,志向非凡。也颇读兵书,兼习兵马,乃得为皇上近臣,护驾功高,倒要为人作嫁,替军头们歌功颂德。以我之文韬武略,若掌兵权,必胜彼等几筹!只恨这不全之身……”
宣召完毕,他已是满腔妒火,无处发泄。却见郭子仪当殿向皇帝交还兵符,又受嘉赞,三角眼一转,心头顿生一计,暗对殿中监李辅国道:“五父,此番朝廷大劫,实起于藩镇军头作乱。如今这郭子仪之权势强于安禄山,且威望较之盛,此时自释兵权,恐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另有盘算,也未可知。”
辅国沉吟,问他有何高见。答曰,不如劝说圣上将兵符授还郭子仪。若他收下,便可见其别有二心,那时再作道理。那殿中监原也十分妒忌功臣,一拍即合。虽然料想皇帝未必答应,但试试无妨。不想李亨欣然应允,便有方才一幕。
依朝恩推想,兵权乃武人心心念念,岂有送到手而不受之理。于是一心指望“香饵钓鱼”,再安排“刀俎”,以泄心头妒火。却不想姜是老辣,那郭子仪竟当众坚拒鱼符,几乎令他难以收场。
回宫路上,鱼朝恩咬牙切齿,肚中愤恨。只是将到宫门时,忽然想起方才在朔方大帐外,听得几个军头互不服气,尤其是李光弼那句“某且相忍为国”,又让他灵光再现:此番皇帝大肆封王赐爵,实因国库早已空虚,无实物可赏功臣,只能将虚名空衔安抚军心。我若将这班军头争执之言述与圣上……
鱼朝恩此时恐也未料到,他这长舌邪臣竟令皇帝李亨一错再错,生生将已收复之洛阳及大片国土拱手让与史思明。
再说李光弼返回太原,不久得报两件大事。
头一件,范阳史思明派其心腹,信都太守乌承恩奏报朝廷,他已将安庆绪派去暗杀他的阿史那承庆拘禁,李立节等斩首,收编了随同五千精骑。同时奏表,愿以所辖十三郡及近十万兵马,连络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同降朝廷。皇上览奏大喜,即封思明归义郡王,御史大夫并范阳长史兼河北节度使等要职。其子史朝义等七人皆封显官,敕令讨伐残贼安庆绪。
又一件,朝廷赦免洛阳王维、郑虔等失足伪官之罪,并赦浔阳狱中李白“追随永王李璘叛乱”之死罪,狱中等候发落。但皇帝不听李岘及郭子仪等力劝,决意严惩押在长安的三百余名伪燕大臣。先是达奚挚等“世代食国禄,受国恩,却叛国附逆”二十一人,被牵至京兆门一棵独柳树下,脱尽衣衫,令百僚观看,当众羞辱,而后杖毙,家眷人口官卖。又将陈希烈等七人稍存体面,赐大理寺内自尽。余者受杖刑、流贬不等。
光弼闻报,忧心不已,百思不得其解:朝廷为何对安史首恶之一如此皇恩浩荡,却将被迫降贼的大唐旧臣斩尽杀绝?那史思明凶虐如豺,岂是朝廷抛给几块肉骨头便可易其本性。那贼只待觑准时机,必然复叛。更可叹,对前朝名相陈希烈等处以极刑,定会令那班尚且身在贼营,仍思归朝廷之百官望而却步,徒增肃叛阻力。然这一节已是无可挽回。当务之急是奏明皇上:“思明不足信,若不根除,国无宁日。”只是此贼奸猾如蛇,出手狠准,又拥重兵,非智取不可得。
何人可担此险任?
光弼苦思良久,终究想到一个人,就是自己先父之同僚,并有世交的先平卢(辽宁朝阳)节度使乌知义之子,少年时的剑友,乌承恩。
人尽皆知,战乱之初,这身长八尺有余的赫赫猛将信都太守乌承恩竟然降贼,是因史思明设下奸计,掠其老母及妻儿,以一家老小性命相威逼而无奈屈降。想必其心中定是深恨思明,欲除之而后快。且喜听说如今史贼对他亲近信任,岂非容易得手?
可是,又有何人能与之联络而不引史贼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