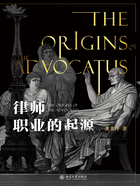
第二章 “业余的”雅典法庭审判
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森认为,如果原则上想让所有公民都能发挥平等的作用,就必须遏制由政治倡议发起者和行政官形成职业集团的苗头,因为如果部分人是门外汉而另一部分人是专门人才,那么专门人才总会占尽上风,使得民主体制蜕变为寡头政体。这个基本原则被应用到了每个涉及法律官司或审判的雅典人身上。1因此,雅典法庭2对法律人的职业化充满了敌意,甚至决不允许专业人士或者内行参与诉讼过程。当然,在特别重要的案件中,我们偶尔也能看到一些专业人士的参与,但绝大多数都不是职业人士。因为在雅典人看来,只有将整个法治体系设计成便于业余者参与的体系,才能保证所有公民的参与。雅典人更愿意让作为纠纷裁判的陪审员来酌情裁决,以体现所谓“民主”,因为这些不懂法律的人更能代表那些对立于精英阶层的平民,并且在没有法律的时候对法律进行解释和补充。3
雅典的法庭并不像罗马一样有固定的场所,审判有可能在整个城邦的各个建筑中进行。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是公共诉讼还是个人诉讼,雅典的法庭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教育者角色。也就是说,每一次判决结果都会教导城邦公民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汉森将雅典的法庭审判比喻成一出“三人剧”,发起诉讼的当事人、进行裁决的陪审团以及主持庭审的行政官员都由“业余演员扮演”。4当事人、审判员和执法的行政官员都不是法律专业人士,甚至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外行,其目的只是保证雅典人单纯的“民主执法”的愿望。尽管如此,修昔底德却提到,雅典城邦的人民对于诉讼是非常狂热的,甚至有人嘲笑雅典人的诉讼案件比其他所有希腊人的加起来还要多。按照汉森的研究,雅典人一年开庭的时间从175天到225天不等,每天可能有4个到40个案子被开庭审判。5阿里斯托芬也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嘲笑雅典人对诉讼的热衷,他的作品《鸟》(27—48)甚至生动地描述了雅典公民对于参加民众法庭活动的积极性:
我们的病跟游牧人相反;他没有国家,硬要取得公民权,我们是国家公民,有名有姓,也没人吓唬我们,可是我们迈开大步,远离家乡,并不是讨厌这个国家,它又强大,又富足,谁都能随便花钱;就是一样,那树上的知了叫个把月就完了,而雅典人是一辈子告状起诉,告个没完;就因为这个,我们才走上这条路,路上带着篮子、罐子、长春花,游来游去,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好安身立业。6
(一)诉讼当事人
根据诸多文献记载,雅典的诉讼发起程序采用“原告制”,即由寻求裁决的诉讼当事人启动司法程序。每项起诉都必须由一名普通公民代表自己或公众利益提出并完成,并不设立国家公诉人。尽管原告和被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纯粹的业余人士,但是“当事人都必须亲自出庭进行辩护”,不允许辩护代理,除非该项起诉涉及代理人本人的利益。7最早的时候,只允许受害方发起诉讼,梭伦改革后允许公民因为公共利益或者正义帮助而代表受害方提出控告。8但是同时也规定控诉权不得滥用,如果公共诉讼(graphe)中的控告人提出的指控不能获得陪审团表决五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数,他将被处以1000德拉克马的罚款并被剥夺部分公民权。9
当事人必须亲自出庭,控辩双方都必须亲自出席案件审理的全过程。按照昆体良的论述,花钱雇人充当法庭辩护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10控告人与被控告人、原告与被告需要在固定时间内对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进行相互论证,并用叫作“水钟”(klepsydra)的工具计时。在案件审讯的过程中,诉讼当事人的演说时间并不长,双方论证之后还需要依据古希腊法律规定进行各自的独立陈述。11当事人可以自由地(至少在理论上自由地)使用他自己的方式阐述案情和解释案件,这对整个城邦至关重要。12但是他们必须以平实的方式向法庭陈述导致法律纠纷的问题所在,特别是在重要的公共案件中,诉讼当事人必须直接陈述案情,而法庭演说环节是在讨论犯罪行为的时候才开始的。
在作意见陈述的时候,当事人必须自己提出意见,而不能通过律师或者代理人来代为完成。不过,当事人似乎可以在获得民众法庭同意后,将自己的陈述时间分配一点给作为辩护帮助人的亲属或朋友以帮助发言,但是绝对有区别于法庭上的诉讼代理人。在政治审判时,这种辩护帮助人甚至可以有多名。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一种靠为他人撰写法庭演说词而谋生的职业,即演说写手,但是由于违背雅典民主的本质而没有获得社会地位。另外,为了保障每个不法分子都可以得到审判,法庭上还允许甚至鼓励“职业原告”利用自己的公民起诉权发起诉讼。这三类人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介绍。
(二)民众法庭
按照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描述:在雅典的法律体系中,由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dikasteria)共同行使权力,公民大会是立法机关,民众法庭则负责裁决。就法庭审判而言,案件的最终结果不是由某个专职法官裁判,而是由数百甚至上千人组成的庞大陪审团共同决定。13这个陪审团即被称为民众法庭,是对等于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国家机构,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
关于民众法庭的设立时间,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14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的记载,民众法庭由梭伦设立;斯坦利(Stanley)认为是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创立了民众法庭;15约翰·索利则提出民众法庭由克里斯提尼进行民主改革时所设。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可以确定的是,大概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或者稍晚一点的时间,民众法庭从一个单独的国家审判机构“Heliaia”转变而来,其目的是分担公民大会无法应付的诸多案件。作为公民行使审判权和接受民主训练的场所,民众法庭的职权在历次政治改革中不断扩大。民众法庭不仅逐渐代替了行政官员对案件的审理,而且也分享了贵族元老院的司法权力,成为雅典城邦主要的司法决策机构16,几乎拥有对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并兼有部分立法权。17它不仅处理私人之间的法律纠纷、刑事案件,而且进行政治审判,同时包揽了许多诸如监督拍卖公共建设工程、见证公开拍卖罚没财产等行政职责。18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众法庭“对于加强民主做出了最大贡献”。
成为民众法庭的陪审员必须要满足如下条件:
(1)年满30周岁。陪审员通常从30周岁以上、没有国库债务的雅典全权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19因为古希腊人认为,男人在壮盛时期(30~35岁)可以接替老父的事业。20作为有着良好信誉的普通城邦公民,陪审员被认为没有必要经过特殊训练就可以对法律纠纷进行裁决。相反,将一个经过专门培训的独立法官或者训练有素的辩护人引入法庭的诉讼程序,会被视作对公民的直接民主权利的侵扰。21
(2)通过抽签遴选。雅典城邦的民众法庭由6000名公民组成,通常是十个选区各选出600名。为了防止不公,陪审员并没有固定具体的审判岗位,而是在审理案件的当天通过抽签的办法确定。希望成为陪审员且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在每年年初参加报名抽签。陪审员的任期为一年,不得连选。不同的案件有不同规格的陪审团,陪审员的人数也不同,一般刑事案件视情况由501~1501人的陪审法庭审判;民事案件则由201人的陪审法庭审理22,当案值超过1000德拉克马时,陪审团人数就会增至401人23。这样的人数规模几乎可使雅典城邦公民在一生中至少被选任一次。
被抽中者必须登上城外的阿托斯山丘,参加就职宣誓仪式,方可成为民众法庭成员。宣誓内容如下:
我将根据公民大会及五百人会议通过的法令投票。之于无法可循的案例,我将尽我所能作最佳裁判,不偏不倚。我将仅就该法内容投票判决。我将公平无私、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证词。24
获得资格的陪审员还可以获得一张作为资格证明的“陪审员证”。据说,起初这种票证是木制的,到公元前4世纪改为铜制,上面印有陪审员的全名及神鸟猫头鹰符号的正式公印。
在当事人陈述完成后,法庭不再讨论,直接进入表决阶段。即陪审团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原告和被告中得票多的一方获得胜诉。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官主持和查问证人证言等环节,当事人连续地陈述事实之后,审判员即刻作出判决。这种裁决方式既没有陪审团的讨论和合议,也没有对裁决理由的说明。陪审团成员通常依据自己认定的事实或理由投票表决,或者通过在瓮中投放铜饼或鹅卵石来判定有罪或无罪。他们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法律训练,审理裁判由一些未经专业技术和司法技能培训的公民进行,民众法庭的辩论也和公民大会一样,目的是打动乃至征服听众和陪审员,一些有煽情鼓动之雄辩口才的演说者的辩词反而成了决定诉讼成败的关键。25这极可能是因为,不同于荷马时期的长老们,雅典法庭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权威,也就是它不需要通过给出判决的理由来寻求公众的赞成。26虽然这种方式排除了陪审团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实质上也加大了因个人感性而冲动作出决定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民众法庭审讯不会超过一天,很多个人案件用的时间比这还要短。27
亚里士多德提到,陪审员是可以获得报酬的,而且认为这是“激进式民主”的基础。但汉森指出,陪审员津贴制始于公元前451年伯里克利颁布公民法之前,法院迫使城邦向公民支付报酬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人来充当陪审员。显然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阿里斯托芬在《马蜂》中提到过,一个热衷于审理案件的老人不得不大清早赶路,因为可以得到陪审员津贴。28
实际上,“担任陪审员的雅典人,并不仅仅是法庭上建立社会典范的被动观察者,而且还是这一过程的积极参与者。……通过这种途径,雅典的法庭不但为解决个人的纠纷提供了一个审判的地点,而且提供了表达以及证实集体意愿的机会”29。
民众法庭制度不仅是城邦民主和公民共治的表征,而且是捍卫城邦民主强有力的武器和坚固的堡垒。它充分体现了城邦民主体制构建的机会均等、全民共治的政治参与精神,但同时作为公众舆论的工具,却不可避免地使法律与政治无法保持合适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崇高地位。30
(三)证人和证据
虽然早在古典时代就出现了对抗式辩论,但是在雅典的法庭中,证人的角色相对受到约束。他们并不是被要求以陈述者的身份去述说发生的事情,而是通常在诉讼当事人完成陈述后对陈述中的细节做出证实。
不过,任何自由公民,包括非雅典人,都有资格成为目击证人31,他们不仅有资格,而且在受到传唤时还必须履行作证义务。从约公元前380年开始,虽然所有供词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书记员宣读,但证人也必须出庭,通过亲临现场来增强其供词的真实性,并且面对可能发生的作假证的指控。奴隶的口供必须是在刑讯逼供(basanos)下作出的才有效,这种刑讯必须在征得奴隶主人的许可后方能进行,而且必须在得到控辩双方同意后才能将从刑讯中得到的信息作为证据予以采用。32而女性根本不被允许进入法庭,若某名女性握有重要证据,只能以起誓的方式将证词提交给陪审团33;女性的证据同奴隶的口供一样,誓言式证词只有在得到对方同意后方可作为文件在法庭上宣读。34
由于这一时期的雅典城邦是典型的口述社会,法庭审判中没有严格的规范程式,整个审判过程好比一场“浓妆艳抹”的演出。无论是早期对所有的法律纠纷具有裁决权的行政官,还是改革以后承担裁判功能的民众法庭,都不是法律精通者。而诉讼当事人在法庭的演说中,则完全不以“相关性”为准则进行论述。无论是在公民大会上,还是在民众法庭中,民主政治的规则都是让演说家们在竞赛中相互攻击,普通公民则充当裁决人。法庭判决的执行由行政官负责,行政官以抽签方式产生,一年一任且不得续任。35对于有明确处罚措施的犯罪案件,依据法律来判罚。但是碰到没有法律可以适用和处罚罪犯的时候,控辩双方均可以提出一个惩罚办法,由陪审团来进行选择。雅典人民民主执政的愿望在雅典法庭审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学者甚至将雅典定义为“法官城邦”,认为在当时再也没有哪个地方像雅典市民那样能够有这么多的时间花费在审判当中。36这种雅典民众所追寻的“民主”,其本质却是法庭审判的“业余性”。
孟德斯鸠为雅典的“业余”法庭找到了合理性解释:“人民不是法学家,并不全然懂得有关裁决的所有修改或变化,所以应该只向他们提出一个对象,一个事实,一个唯一的事实,让他们决定应该判罪、应该免罪还是下次再审。”37也就是说,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又或是法官,都不需要具备专门的法律能力。在他们看来,精通法律的职业法官或者训练有素的辩护人,一旦进入法庭审判,会影响民众的直接民主权利。如果想让所有的公民都能够参与城邦政治,就必须将整个法治体系设计成由业余者来操作。实际上,雅典人民一直在竭力阻止法庭审判的职业化。所以有学者认为,雅典的法庭审判“完全是两个诉讼当事人的口头较量,他们争先说服庞大的普通观众、匿名的城邦公民投票支持他们,反对他们的对手”38。这正是雅典法庭的独特之处,即“法庭在任何层面上都不赞成职业化”39。
1 See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9. 中文译本请参见〔丹麦〕摩根斯·赫尔曼·汉森:《德摩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何世健、欧阳旭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2 关于古代雅典的法律制度,请参见Arnaldo Biscardi, Diritto Greco Antico, Giuffrè, 1982, 264ss.; Michael Gagarin, Early Greek Law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driaan Lanni, Law and Justice in the Courts of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参见徐爱国:《法治理念:从古典到现代》,载《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1期,第32—34页。
4 See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9, p. 180.
5 See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9, pp. 186-187.
6〔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古罗马〕普劳图斯、〔古罗马〕维吉尔:《鸟·凶宅·牧歌》,杨宪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7 John A. Crook, Legal Advocacy in the Roman World , Duckworth, 1995, p. 33.
8 Arist. Ath. Pol. 9.1.
9 Demosthenes 53.1.
10 Quint. Inst. Orat. 2.15.30.
11 参见〔德〕乌维·维瑟尔:《欧洲法律史:从古希腊到〈里斯本条约〉》,刘国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12 See Lene Rubinstein, Differentiated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the Athenian Courts, in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5-136.
13 Arist. Ath. Pol. 130a.11–12; Ath. Pol. 53.3; Ath. Pol. 68.1.
14 丹麦哥本哈根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汉森认为,梭伦改革创建起来的一个单独的国家机构叫作“ Heliaia ”,和公民大会并列,并不附属于公民大会,是由抽签选举的陪审员组成的。Heliaia在古风时期曾是唯一的法庭,其他行政官有案件需要审理时就从司法行政官那里临时借来一用。Heliaia能够被分成不同的法庭审理案件,到了演说家时代,Dikasteria(民众法庭)这个术语才替代了Heliaia。哈蒙德认为是伯里克利完成了从Heliaia到Dikasteria的转变。约翰·索利却提出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促成了民众法庭这种形式上的改变。由于梭伦的司法改革措施没有留下直接的史料证据,西方学者的结论往往建立在词源学考据以及对铭文和演说词进行推论的基础上,所以这一问题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参见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 ,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01;〔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5 See Stanley B. Smith,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925, vol. 56, pp. 106-119.
16 See Christopher Rowe and Malcolm Schofiel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1-134.
17 参见沈瑞英、杨彦璟:《古希腊罗马公民社会与法治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18 See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9, pp. 179-180.
19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6页。
20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98页。
21 See Harvey Yunis, The Rhetoric of Law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in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95-196.
22 参见沈瑞英、杨彦璟:《古希腊罗马公民社会与法治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23 See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9, p. 187.
24〔英〕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王琼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25 参见沈瑞英、杨彦璟:《古希腊罗马公民社会与法治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83页。
26 See Stephen C. Todd, Law and Oratory at Athens, in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8.
27 See Stephen C. Todd, Law and Oratory at Athens, in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7-111.
28 参见〔古希腊〕阿里斯托芬:《云·马蜂》,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7、175页。
29 Matthew R. Christ, The Litigious Athenian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0. 中文译文参见〔美〕加加林、〔美〕科恩:《剑桥古希腊法律指南》,邹丽、叶友珍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
30 参见沈瑞英、杨彦璟:《古希腊罗马公民社会与法治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31 Demosthenes 35.14.
32 Demosthenes 49.55.
33 Demosthenes 39.3.
34 See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9, p. 201.
35 Arist. Ath. Pol. 1298a 30-2.
36 参见〔德〕乌维·维瑟尔:《欧洲法律史:从古希腊到〈里斯本条约〉》,刘国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3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4页。
38 Harvey Yunis, The Rhetoric of Law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in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6.
39 Stephen C. Todd, Law and Oratory at Athens, in Michael Gagarin and David Cohen(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Greek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