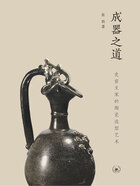
序 形式的中国
15世纪出版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中,标志着中国的是两个位于当时已知世界最东端的国家,其中北方的国家叫“塞利卡”(Serica),南方的国家叫“秦尼”(Sinae)。这种地理知识并非文艺复兴的发明,而是文艺复兴作为目标所复兴的古代知识之一,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50年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所著的《地理学》。“塞利卡”的意思是“丝国”,即生产古代世界奉若拱璧的珍宝——丝绸的国度;“秦尼”则来自一个真实国家的名称,今天的大部分学者均同意,它应该是古代东方世界闻名遐迩的强大王朝“秦”的遗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中国作为“丝国”依然故我,标示物质文化形态的“Serica”的名称却逐渐淡出,被人遗忘。长期以来,西方世界流行的标准称谓是作为地理名称的“Sinae”一词——其异写形式或“Sina”或“Chine”,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其英文表达形式“China”。有意思的是,到了17世纪,“China”也再次获得了类似于“Serica”那样的物质文化形式,但这一次不再是“丝绸”,而是中国的另一种骄傲——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的高端舶来品“瓷器”(chinaware),也令中国变成了一个梦幻般的“瓷国”。
然而在中国本土,瓷器从来都不是梦幻,而是一种真实存在。至少从商代中期开始,具有瓷器基本特征的原始青瓷已粉墨登场,这使得瓷器几乎与中国文明同时诞生。作者嘱我为他新出版的“小书”作序,尽管这部书的篇幅不足200页,却因为所处理的题材,具备了成为一部“大书”的资格。通读全书,我强烈而鲜明的是以下四个印象:
首先,本书在方法论上与坊间汗牛充栋的相关读物都有所不同,探索了对作为“艺术品”的中国陶瓷进行“艺术史”研究的路径。这种路径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陶瓷的造型问题上。在作者看来,陶瓷与绘画、雕塑一样,都属于造型艺术的行列,可以用艺术风格学的方式来加以把握。例如,作者注意到,早期陶瓷的器形存在着有意偏离功能的倾向,“转而去突出不合逻辑的结构形式与非实用目的的外观美感”,正是这种诉求成就了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中蛋壳黑陶杯那纤细脆薄、空灵精细、令人叹为观止的造型之美。值得称道的是,在强调造型的同时,作者并没有过度夸大艺术家主观的艺术意志,而是将其放置在与不同材质和媒介相持相让的适应过程中加以动态描述。书中以大量的案例,揭示了陶瓷始而模仿金属器(商周青铜器、隋唐金银器),进而融合金属器的器形和纹饰,终而在造型、纹饰和釉色各方面,均创造出以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为代表的那种登峰造极的杰作的完整过程。
其次,本书在年代上仅仅叙述到宋代,对于中国陶瓷史后半期辉煌的青花瓷和彩瓷时代不置一词,显属有意为之。宋代的物华天宝,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终结和近世文明开端的标志,无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上述年代序列的选择,犹如一次腰斩《水浒传》的行径,使中国陶瓷史在其第一个高峰期的花好月圆之际戛然而止,正是为了刻意宣示,前述从模仿、融合到创造的艺术生产过程已然完成。
再次,本书具体论述了这一生产过程的三个阶段,亦属匠心独运。第一个阶段在中国南(楚、吴越)北(中原)文化互动的语境下,讨论了商周青铜器与原始青瓷的跨媒介模拟与转换;第二个阶段在东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下,追索了隋唐陶瓷器与西方(波斯、粟特)金银器的交融与汇合;第三个阶段在古今对话的语境下,探寻了宋代陶瓷以复古为创新的伟大成就。三个阶段将陶瓷的艺术生产,放置在跨地域、跨时间、跨文化和跨媒介的宏大背景与动态关系之中,生动地诠释了古典时期中国陶瓷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它是上述空间和时间场域各种因素大开大合运动进而交叉辐辏的结果——这一点,不仅在隐喻的意义上,更是在现实中,正如实际中国的形成一样,使中国陶瓷成为另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China),一个“形式的中国”。
最后,我想指出,正如本书作者的艺术家身份所示,本书的写作对于陶瓷/中国之形式意义的阐发,也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造力,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在这种意义上,本书的写作不仅具有学术的意义,更具有实践的意义。作者范勃近年来的一系列艺术创作,如《潋滟》(2017)、《回到现场》(2019)、《无形的剧场》(2020)等,始终贯穿着对于跨媒介之“物”如盲文、药丸、针筒、实验室的迷恋,以及对于中国境遇的处境感;这种“恋物癖”和处境感被用于展现作者的形而上观念,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器之道”。
但是,作者在本书中对于陶瓷、中国、创造力三位一体的历史与哲学思考,居然从未付诸其艺术实践,这颇令我诧异。或许这意味着一个伟大计划的肇始?这使我对于他未来的创作潜能,充满着期待。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李军
202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