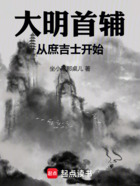
第75章 内外埋祸 严嵩思策
严嵩的府邸中。
这天将到酉时的时间,待客的前厅中坐了两个人,堂上坐着的,自然是严嵩,堂下坐着的则是赵文华。
在赵文华旁侧的案桌上,放着几份邸报,这些邸报他都还认得,就是几天前经他的手递上去的。
待他坐定之后,严嵩摸着长须,吩咐道:“你把这些邸报念一下。”
赵文华知道,严嵩每逢做出这个动作,就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当即不敢有丝毫拖沓,赶紧遵命去念一份邸报上的条陈:
“科道官卢勋、陈储秀劾:原任山西平阳府知府升山西按察司副使聂豹,先以虏寇太原,借口军兴大括部民财,多者千金,少者数百几十,约入银三万二千六百余两......”
赵文华念完之后,并没有发觉什么问题,朝着严嵩干笑了一下,却见严嵩正在敛目凝神,木头人一般,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得咽一口唾沫,继续开始念第二份:
“灾祸四川,成都府所属税粮有差,仍命有司出官粮赈济,奏请免去税额。”
接着又是第三份。
“灾伤昌平霸滦三州良乡房山大城,实坻昌黎各县及蓟州营州各卫罗文谷等关税粮有差......”
念着念着,赵文华的心中就越发没有没有底气,他不明白严嵩为何要将这些邸报带回来,还要让他当面念一遍。当把最后一句念完之后,他一边端起茶杯喝茶,一边看向严嵩问道:
“父亲,这几份邸报可是有什么问题?”
严嵩一直关注着赵文华表情的微妙变化,冷了一会儿场之后,才开口问道:“枉你自诩聪明,跟在我身边这么长时间了,怎个还明白?我问你,皇上修玄修的什么?”
气氛被调节得如此紧张,赵文华生怕答错了,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话来。
“修的是天降祥瑞之事。”严嵩接着叹息一声,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再说道,“你这报上来的,不是敛财,就是灾祸,哪件事跟祥瑞沾边了?”
赵文华终于“哦”一声,恍然大悟。
“不仅你要明白,你也要想办法,让那些地方的通政使明白,事情应该怎样办,奏疏都该奏些什么,不要总是向朝廷喊穷喊灾嘛!”
“明白。”赵文华当即答应,“这件事情儿子明天上值就去办。”
“最近你那边可有什么动静?”严嵩终于松一口,喝了口茶,“老夫这边不接客,都往你那边去了吧?”
“是来过几拨人,但说的都是官面上的话,说到底,他们还是怕父亲坐不稳这个首辅之位。倒是兵部尚书王以旗来了好几次。”
“王以旗这人,是个望风使舵的主,当日在廷议未开始之前,他还是支持夏言的,当了廷议结束之后,竟就急着往内阁来拜访老夫了,这种人不可重用。”
严嵩说完这一句,又想到了仇鸾,问赵文华道:“仇鸾近来可有做了什么事情?”
“他呀,自从接了东楼教出来的那几个乐伎回府之后,整个人走路都是飘在天上的。”赵文华主动上前,将厅堂中的火盘往客厅中央推了推,“要我说,他的胆子也比我大不上多少,自从策划了那件事之后,门都不敢出了。”
“这件事情,就怕姓曾的会找到什么线索。”
想起当初严世蕃跟他说的,要将曾铣留在三边总督这个位置上,一直到现在,严嵩都还有些担心。
但事情的详细经过是仇鸾一个人策划的,旁人都难以知道,自然也难以洞察其中是否会留下把柄。
可他就是一直都觉得,将曾铣留在边境,始终是个“雷”。
“曾铣留在边关确实难以让人痛快,但这件事情关乎他仇鸾的生死,想来他会小心谨慎的。”
“这个仇鸾也让人痛快不到哪里去,行了,若是没有其他的什么事情,你也早些回去吧,记住交待你的事情,要尽快办好。”
赵文华愣了一下,应声退去。
朝夕如流光阴荏苒,日子不知不觉走到了十月中旬。
小冰河时期,京城的头场雪要比寻常时期来得早一些,今夜也是小雪飘飞。
严嵩望着外面漂落的雪花,陷入了沉默。
他代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严嵩接下的这个首辅之位,可谓是难上加难。
这个难倒不是说,他现在往内阁值房一坐,看奏疏邸报、与晋见的官员谈话等诸多事宜不顺心,而是难在不知如何去讨好皇上。
夏言在位时还好,整天想着边境之事,不用顾忌这些事情,但他要想的就多上许多。
不过。
就算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中,他还是办好了两件事情:
一是告知王以旗管好边将诸事,没有什么大事情,不要轻易惊扰皇上静修;二是让工部抓紧修缮西苑的道宫,皇上要修玄的事,当作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处理,要多少银子,尽管提。
前者是为了压下夏言在任时留下的影响,而后者相对来说,则更为重要,应该作为以后各部官员的主要工作。
永乐皇帝定都京城后,钦定百官依职掌权力划分,共有九大衙门、九小衙门。
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翰林院、国子监、尚宝司和苑马寺。
九大衙门的掌印者,习惯上称为九大卿;九小衙门的主管,俗称为小九卿。
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所谓首辅,自孝宗时代起,实则上就是通过这十八大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现在大理寺、通政司、都察院这三个衙门,算是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
至于其他的,那些人刚刚经过夏言落台的事情,明面上虽然都是与他靠近,但毕竟皇上正式册封他为首辅的圣旨还没有下来,这些人实则上都还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为了避免让皇上产生疑心,严嵩现在还不敢尽数去撤换这些人,换上先前被夏言撤换的那些亲信,只是向外面表态:
不以自己的喜好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照才能推举部院人选。
这也是徐正卿跟他提出的一个建议。
这种话说出来,尽管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严嵩会如此做,但该表明的态度,还是要表明的。
大小九个衙门,哪个人没点自己的小九九?
在两京当官的人都知道,这官要跟着首辅走的。
如何能在不大面积置换人员的情况下,一次性笼络这些人,又涉及到徐正卿提供给他的第二个建议——察京。
所谓察京,就是对应天、顺天两京官员实施考核。
四品以上的官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都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淘汰。
现在的严嵩,确实急需去培养一批班底党羽,这个办法也的确是最实用,能最快速能形成他的班底的,但他还是觉得太急了一些,动静太大,还要惊扰到皇上,所以他一直摇摆不定。
这件事情他也和严世蕃商量过,但严嵩看得出来,他这个儿子,看重的不是别的,而是那些官员口袋中的银子,所以话也不能全听。
仔细权衡过后,严嵩又站了起来,走到方才赵文华落座的椅子前,拿起了放在最底下的那份邸报,喃喃自语道:
“聂豹、聂豹,你什么时候出事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