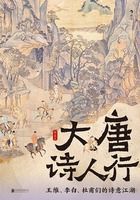
第5章 《神童组合 笑傲悲歌》:江东布衣骆宾王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
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初唐四杰”名声煊赫。不过,要理解这个名号,还应将其分拆为“初唐”和“四杰”。
“初唐”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时间跨度从大唐建立到七世纪末,前后共包括六位皇帝: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周女皇武则天、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这是一个国力逐步攀升的过程,文化也日渐兴盛,似乎就是一条通天大道。但这里面隐藏了一个问题:盛世之路一定是个人的幸福之路吗?
“四杰”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天才,都有神童之誉,但他们绝非“少年天才组合”。因为年龄委实相差太大,甚至难称同一辈人。骆宾王比卢照邻约年长五岁,卢照邻又比王勃、杨炯年长十余岁。
“王杨卢骆”这一排名,并非依据年龄,那么依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生活在后世称颂的大唐治世,一边获得美名,一边遭受鄙夷。“轻薄”是他们共同的标签,一位以知人善用而著称的官员直斥他们“浮躁浅露”,这又是为什么?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以才华笑傲文坛,却一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甚至难求善终,其间又有着怎样的悲欢?
在“王杨卢骆”之前,世人眼中的诗人是皇帝和宰相们,高高在上,穿紫着绯,一呼一吸都有宫廷味,张嘴就是优越感。相形之下,四杰的官位实在微不足道,但他们却凭借一身飘零和绝世才华,让此前那些帝王将相的诗作低到尘埃里。
正是他们,让唐诗拔节而起,冲向新高度;也是他们,让后人看见了唐诗气象。
如果说李世民和虞世南们的诗是用金粉写的,那么初唐四杰的诗就是用生命来写的。在文学这杆大秤上,任你有何头衔,都无法虚报斤两。
——
贞观二十一年(647)秋。长安城东,春明门外。
“骆宾王?名字挺响亮嘛。”满脸褶子的城门吏看了一眼递到手里的公验文书,又瞅了瞅眼前这个体格壮实的黄脸书生,轻声嘀咕。
“某姓骆,名宾王,字观光,江东义乌人。《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某来长安,只想用这一身本事辅佐君王。”黄脸书生朗声道。
“你们这些举子……”城门吏笑着摇了摇头,“早日高中啊!”
骆宾王接过文书,抬头看看“春明门”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心头陡然生出一片豪情。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长安。春明门乃长安东城墙的中门,连接着通往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的交通要道。城门两侧是清一色的铁甲卫士,气势凛然。来往官民络绎不绝,进城者皆靠左行,出城者靠右行。“入左出右”,这是当朝宰相马周定下的规矩。
这一年,骆宾王十七岁,一个踌躇满志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来长安之前的那个夜晚,做县令的父亲沉默不语,只有母亲反复叮咛,让他今后多个心眼,学会看别人眼色,把那几个在京为官的亲戚、熟人,挨个都拜访一遍。再去打听一下主考官的情况,看能不能早点结识……他满口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凭我这满腹诗书,自然能遇见识货的。待我取了功名,求个一官半职,还不如探囊取物一般?
他生于贞观之初,是在贞观之治中长大的一代人,对大唐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从小到大,他听到的一直都是好消息,比如:皇帝多么英明,既从谏如流又重用人才;皇帝和皇后多么俭朴,连宫殿都不舍得建,绸缎也不舍得穿;军力多么强盛,大破吐谷浑、高昌,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政治多么清明,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就算犯了罪的人也不会逃跑,而是自动到衙门领罪;体制多么创新,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了农户赋税劳役,天下百姓欢欣鼓舞……
生逢治世,他自觉无比幸运。虽然幼时也经常纳闷:为什么我们义乌骆家庄晚上家家户户都锁门,只有穷得叮当响、住在破庙里的才“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更加不可能,平常就连丢一只鞋都会转眼之间就找不着了。尤其是“均田制”,那么好的政策,为什么我们骆家庄就没实施呢?是不是宰相把这里给忘了?
只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骆宾王从小就不会把这些问题说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出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是个“神童”——神童怎么能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等到长大些,他开始明白:贞观之治是掺了水分的,成色远没有官方口径中那么足。当时,朝廷只对关中地区以及全国各大城市有绝对控制力。在大片乡村地区,真正发挥作用的仍是世家大族。像均田制之类政策并未在大唐全面推广,全国人口仅为隋炀帝大业前期的三分之一,比李渊统治时期也高不了多少,普通百姓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但社会确实稳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百姓们都愿意相信,千古未有的明君李世民,会带领大唐走向盛世。虽然事实上,晚年的李世民并没有那么英明,但经历了隋末乱世之后,还有什么比“相信”二字更金贵的呢?
在“初唐四杰”之中,骆宾王出身最差,却也远非普通百姓。义乌骆氏先祖乃是三国时期的将领骆统,传到隋唐虽只剩下故事,但仍然算将门一脉,世代文武传家。骆宾王的祖父曾在隋朝任武职,父亲则是大唐河南道青州总管府博昌县令。
这里需要提一下,很多人习惯瞧不起县令,说其只是“七品芝麻官”。事实上,唐代的县令绝不是“芝麻官”,而是典型的中层文官。
唐代的县,根据所属区域、人口、经济等条件不同,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县的等级不同,县令品秩和前途也相差悬殊。其中,京都治下的县为赤县,县令为正五品上,而唐代的京都包括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京都附近的县为畿县,县令为正六品上。其余五等县主要根据人口、经济来划分,上县等级次于望县和紧县,县令为从六品上。中县县令为正七品上。下县县令为从七品下。县令之下设有县丞、主簿和县尉,均为“九品三十阶”的流内官。换句话说,都属大唐正式公务员编制。
骆宾王父亲所在的博昌县是个上县,其官品乃从六品上。他三十多岁做到这个级别,已属不易,应该是有才干的,也有前途可言。
骆宾王自幼便有“神童”之称。他从小在义乌骆家庄长大,跟祖父学习剑术,也在乡里读私塾。江南水乡以及家族文化浸染,使他的身上别有一种灵秀之气。七岁时,他对着村口池塘的一群大白鹅,脱口吟出了一首诗: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骆宾王《咏鹅》
这首诗迅速传播开来。村里人只觉得可爱,但义乌县学里的博士听了则大吃一惊,赶紧托人转告骆家祖父:一定要好好留意,认真培养。
九岁时,骆宾王又写了一首诗:
忌满光先缺,乘昏影暂流。自能明似镜,何用曲如钩?
——骆宾王《玩初月》
这首诗传播得更快。如果说《咏鹅》像一缕清泉,只是灵光闪现的话,这《玩月》就像一把小刀,已然初露锋芒。
博士听后喟然长叹:“我苦读大半生,却也写不出这样的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又一转念:“罢,罢,罢,我一老朽,跟人家神童有的比吗?”他禀明县令,将此诗与《咏鹅》一起,镌刻于义乌县衙前的照壁上,供全县人赏读。
一时间,义乌神童名动江东。
就在县令和博士纠结于要不要将这位神童提前破格收入县学时,骆宾王已经离开了义乌,北上至其父所任职的博昌县生活。
博昌地处齐鲁大地,历来藏龙卧虎,“稷下之学”影响深远,响马盗寇亦名动江湖。作为县令公子的骆宾王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少年时光,他同乡里的游侠少年一起纵横驰骋,饮酒舞剑,也同几位江湖野老交友,怡然自得。人们从这位“官二代”兼“神童”身上,看到的是希望。而骆宾王自己也暗暗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有次,几位少年一起畅想未来。在如此清平岁月里,他们都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大家谈得兴起,只有骆宾王不说话。
有人说:宾王,说说你的鸿鹄之志吧!
他笑笑:宾王只想做宾王。
那人有些恼:你是瞧不起我,还是说废话呢?
他还是笑,不解释。
另一人接过话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说的就是你!当朝中书侍郎马周,字宾王,清河郡茌平县人,以敢谏而闻名,有魏徵之风骨。咱们宾王想成为的是他——马宾王。人家可有一颗当宰相的心呀!”
如今,骆宾王终于踏入期盼多年的长安城,住进了紧邻国子监的宣阳坊中一处客栈。他是来应考的,想住得离考场近一点。客栈招牌写着“四方客栈”四个大字,甚是惹眼。房间虽略显逼仄,但价格很合适。长安物价高,父亲并未给他带太多钱来。
骆宾王定下心神,潜心苦读。可未过多久,便听到了马周去世的消息。他心中充满遗憾,却坚信只要有机会,自己定能继承马周遗志。而想要这样的机会,只能靠科举。
武德年间,李渊重用关陇贵族,官员构成主要是关陇贵族子弟以及自隋朝承袭下来的旧官僚。贞观年间,李世民重用了一批山东(崤山以东)的高门大姓,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高门大姓势力广、名望足,甚至压过皇族李氏,也对皇权形成了压迫。于是,他赶忙掉头,从民间选拔人才。他明白,那些毫无根基的寒素士人,会更好用,也更安全。
贞观年间,科举的常规路径包括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和明算六科。这六科之中,秀才科在唐初名望最高、标准最高,难度也最大。且当时规定,倘若被举荐的考生考不上,就会追究州郡长官的连带责任。于是,大多数州郡长官都不敢送举秀才科,应试人数越来越少,到后来高宗朝早期就停止了。但因为秀才的名头好,到玄宗之后,也被用来称呼及第的进士,乃至泛指读书人。
明法、明书、明算三科,分别选拔格式律令、文字书法、数理计算方面的专门人才,但及第者能做的官职有限、品阶也不高,在唐代文献中鲜有记录。出路最好、最受重视的是进士和明经两科。此后,又有了非常规、不定期的选拔人才路径,叫作“制举”。
据说,李世民对自己选拔人才的成果很满意。史书称,他曾“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gòu)中矣!”
“彀”乃箭的射程,比喻牢笼、圈套,显然不是个好词。但能入帝王之“彀”,士人们是挤破头也愿意的。
因缺乏记载,骆宾王第一次所考科目不得而知,推测可能是明经。从家学与知识结构来看,明经很适合他。
明经科要求应试者熟读并背诵儒家经典,包括注疏。共考三场:第一场帖文,第二场口试,第三场试策文。这一科目的最大特点,是考验死记硬背的能力。“帖文”类似于填空题,“口试”类似于简答题,“试策文”类似于论述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前两场,第三场一般只是走过场,在整个唐代文献中,并无一篇明经科时务策文流传下来。
骆宾王对儒家经典很精通。骆氏家传之学是《易经》,他在齐鲁又跟几位经学大师学习过,平时写文章作诗擅长用典故。比如,他在淄川写过一组咏物诗,其中咏秋露的诗是这样写的:
玉关寒气早,金塘秋色归。泛掌光逾净,添荷滴尚微。变霜凝晓液,承月委圆辉。别有吴台上,应湿楚臣衣。
——骆宾王《秋晨同淄川毛司马秋九咏》其四《秋露》
全诗通篇无一字提到“露”,只是堆满了典故,看起来很华丽。
骆宾王自信满满。转眼便过了年,那次春闱,他前两场轻松过关,第三场也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文。这位江东神童、齐鲁才子,自认为能一战成名。然而放榜那天,他把榜单从头看到尾,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
他失魂落魄回到四方客栈,连续两天没有吃饭。客栈的胖掌柜敲开了他的门,端进来一坛老酒、一只蒸鸡、四碟菜蔬。眼前的书生神情呆滞,两眼通红,脸更黄了。
胖掌柜默默斟了两杯酒,自己抬手喝了一杯。骆宾王也默默喝了。胖掌柜继续满,二人继续喝。谁也没说话,就这样对饮了十余杯。
胖掌柜见骆宾王的神情放松了些,像一块冰略略化出了水渍。他微微笑了,轻声问:“骆公子,你可知道自己因何落榜?”
骆宾王摇了摇头。
胖掌柜道:“这客栈中也住着不少外地的举子。不少人都至少提前一年来长安,有的甚至提前两年就来了,你可知为何?”
骆宾王不语。
胖掌柜又道:“想来骆公子也是知道的。我们大唐行的是‘公卷’制度,不但要有学问、会考试,还得有知名度,有王公大臣的推荐书……”
骆宾王知道,“公卷”是李世民定的规矩,考进士科,须“行卷以求公荐”。而所谓“行卷”,就是举子把字写在卷子上,一卷一卷送给那些硕学名儒、公卿将相,以求得他们的荐举。各地举子都要在长安奔走,想方设法结识达官贵人。假如送一次不成,还要送第二次、第三次,叫作“温卷”。有的还直接拜见考官,希望得到垂青。即便最终不成,至少也能混个脸熟。对于这种制度,骆宾王非常反感。朝廷既以科考取士,为何还允许以交际影响考试?这是何道理?
他沉声道:“考进士才要行卷,我考明经,何须如此?”
胖掌柜微微一笑:“公子说的是。但对考官多了解一下,总是好的。可公子来长安后,天天待在客栈里看书、饮酒,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骆宾王冷哼一声。
胖掌柜叹了口气:“骆公子自恃有才,可别人就无才吗?岂可小看了天下人!别的不说,人家都对考官很熟悉,而公子却连考官是何履历、有何好恶都不知晓,岂非自曝其短?老朽且问一句:此次试策文,考的是什么题目?公子又是怎么答的?”
骆宾王一愣,将试题和自己的文章缓缓说出。
胖掌柜点了点头:“公子好一篇雄文!若在平时定能高中,但遇到这位考官——唉!”接着,他一一指出,文章犯了考官哪些忌讳。原来,其中一处甚至提到了考官父亲的名讳,这是公认的大忌——能让人当众翻脸的那种。
对于考生来说,这是无心之失,但考官哪管这些?事实上,为了规避这一点,很多考生会提前打听考官的家谱,以便答题时避讳。
骆宾王倒抽一口冷气,久久无语。倒在这样一篇走过场的文章上,岂能无恨?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那些话固然是母亲所说,却又何尝不是父亲的建议……
胖掌柜不再说话,默默添酒,二人继续对饮。一坛老酒渐渐见底,二人都有了醉意。
胖掌柜忽而笑道:“骆公子,老朽知道你才兼文武,学富五车,只是内心太过纠结:你一方面想做官,出将入相,济世安民;另一方面心底里又瞧不起那些做官的,觉得他们畏畏缩缩,缺少人味儿,想要浪迹江湖,行侠仗义,是也不是?”
骆宾王大笑:“正是,正是!”笑着笑着,忽然流下泪来,“前日收到家信,我爹病了……”
那年暮春,骆宾王顶着瓢泼大雨回到博昌,看见了卧床不起的父亲。大雪纷飞时,他在博昌父老的帮助下,安葬了父亲。母亲跟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哭倒在一旁。
父亲虽为官多年,却两袖清风,并无多少积蓄,全家生计迅速成了问题,而故乡又远在千里之外。好在,母亲稳住心神,带着他开了十余亩荒地,把日子一点一点硬撑了起来。
骆宾王开始感受到一个字——穷。这个字,顺理成章,又抵死纠缠。
他要为父守孝,又要照顾母亲和弟弟。依照儒家惯例,父亲去世,须守孝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其间不做官、不婚娶、不应考。此外还有更详细的规定,比如,禁饮酒吃肉、禁听曲下棋、禁怀孕、禁分家产等。
科举之路,短期内走不通了。
次年,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一个噩耗震动了大唐及四夷万邦——李世民驾崩于含风殿,终年五十一岁。大唐百姓纷纷垂泪,他们无法想象,离开明君的日子将如何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