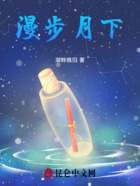
第2章 老店和家
离开霓虹闪烁的美食街,我独自步入暮色笼罩的街道。路灯次第亮起,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投下昏黄的光晕。这条走过无数次的街道,如今既熟悉又陌生,就像翻出一件旧衣裳,明明记得每一处针脚,却再也穿不出当年的模样。
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这条路上,曾印满我不同时期的足迹:童年时蹦跳着数地砖的裂痕,少年时奔跑着追赶末班车,后来则是低着头匆匆掠过每一个熟悉的路口。而现在,那些我以为早已深埋的记忆,正随着每一步踏在熟悉缝隙间的感触,一点点浮出心底。
命运给了我一副令人艳羡的面容,却搭配了一个破碎的家庭。这奇特的组合让我从小就活在矛盾的光影里——女生们热烈的目光追逐着我,而我却只能报以沉默的退缩。
在教室里,在走廊上,那些窃窃私语和偷偷递来的纸条,都让我不知所措。“安静的美男子“这个带着善意调侃的外号,像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我的格格不入,又折射出某种我自己都未察觉的闪光。
那些年,我像一座孤岛,虽然被温暖的海浪不断拍打,却始终无法给出回应。但不可否认,这些青涩美好的心意,确实在自卑的土壤里,悄悄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原来,在别人眼中,我也有值得被喜欢的一面。
岁月流转间,我终于攒足了推开那扇大门的勇气。长久以来的孤僻让我连最平常的理发都成了需要心理建设的大事,于是任由头发野草般生长,在肩头蜷曲成无人修剪的灌木丛。
某个午后,浴室的水汽渐渐散去。镜中的面孔在氤氲中逐渐清晰,我小心翼翼地刮去胡茬,像在修剪一片荒芜的园地。翻出那件自以为最帅气的黑色冲锋衣,布料摩擦声在安静的心里格外清晰。
我没有戴上兜帽,阳光第一次毫无保留地拥抱这个新形象。我随手拨弄了下潮湿的发梢,看它们在光线中变幻出意想不到的弧度——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却总是意外地帅气。就这样,带着些许忐忑与更多期待,我迈出了走向外界的第一步。
我刻意挺昂首挺胸的走在街道上,仿佛这样就能让勇气在骨骼里生长。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路人的目光像蝴蝶般轻轻停驻又飞走。
那些不同年龄的女性面孔在记忆里格外鲜明:捂着嘴轻笑的大学生,拽着闺蜜衣袖的少女,还有牵着妈妈手却频频回头的小女孩。她们假装专注前方的样子如此可爱——如果忽略那些不断飘来的余光,和同伴间突然响起的窃窃私语。“快看““帅哥“这些零星的词语,像偶然落入掌心的花瓣。我不确定它们的含义,却能感觉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舒展。
午后的阳光里,那个曾经蜷缩的少年,正学着把脚步迈得越来越稳。就这般,我走出了少年时的黄昏。
不知不觉间,我的脚步停在了一家熟悉的店铺门前。时光荏苒,老板已经认不出我了。我点了一份记忆中的套餐:一根大的出奇的牛棒骨,一碗清亮的原味米粉,还有一张烤得金黄酥脆的馕饼。
这味道简单纯粹得近乎固执,没有多余的调味,却没有任何调料可以比拟,牛骨在岁月里慢慢熬煮出的醇厚。当第一口热汤滑过舌尖,那些在外漂泊的日子突然变得真实可触。原来最深的思念,一直藏在这碗不曾改变的老味道里。
这是我第一次在傍晚时分来这家店用餐。从前那份体面却耗时的职业,总让我归家时已近凌晨。那时我独居在一套中西合璧的三居室里——那是爷爷奶奶最纯粹的爱与不舍。
这套宽敞精致的房子,承载着太多我无法承受的重量。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从小和父母的见面屈指可数。而二老的离去又太过突然,连好好道别的机会都未曾给我。无数个深夜,空荡的房子都回荡着我压抑的哭泣。
从前我不止一次的问过,为何有着可观退休金的却要过得如此清贫,他们却只是笑笑不说话。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对生命无常的清醒认知,在不知还有多少个的明天里,他们省吃俭用,只为给走后孤苦的我留下他们认为最可靠的保障,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可他们不知道,当生命中最温暖的灯火熄灭后,我已经没有家了。
那段时间,变故接踵而至。失眠成了常态,而我不愿总在空荡的房子里独自面对漫长的黑夜。于是,那家深夜仍亮着灯的老店,成了我的去处。
其实凌晨时分并无食欲,但出于礼貌,我总会点最小份的牛肉汤——汤多粉少。蜷缩在角落的窗边位置,看着碗里升起的热气在暖光下氤氲成雾。偶尔啜一口温热的汤,更多时候只是望着窗外沉寂的夜色出神。蒸腾的热气与冰凉的玻璃之间,是我无处安放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