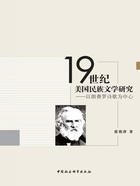
三 朗费罗及其《海华沙之歌》在19世纪美国民族文学中的地位
朗费罗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诗人。朗费罗的诗歌既受到精英人士的推崇,又在大众中广为流行。他的作品被广为传颂,一些作品入选学校课程,一些作品进入了家庭和公共生活空间。他的许多诗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在同时代的英美诗人中,没有谁的作品能被那么频繁地引用,即使丁尼生和白朗宁也不例外。朗费罗在世时,就被美国知识界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霍桑将朗费罗称为美国本土诗人中的领头羊,豪威尔斯则认为朗费罗可以与丁尼生、白朗宁媲美,爱伦·坡则反复提及朗费罗的“天才”。他的其他崇拜者还有惠特曼、亚伯拉罕·林肯等知名人士。在其后半生,朗费罗已成为美国文化成就的象征。在1881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全国的学校以朗诵和表演的形式为他庆祝生日。诚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像朗费罗一样在生前就得到如此全面的认可。朗费罗不只在美国享有盛誉,他也是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个美国诗人。他不仅在英国拥有读者,而且他的作品经过翻译后得到了欧洲和拉丁美洲读者的欢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格兰,他的声誉最终超过了丁尼生和白朗宁[41]。他被英国人视为他们伟大的诗歌经典大师中的一员,他们授予他牛津和剑桥的学位。而维多利亚女王曾邀请他一起品茶,在其他诗人中仅有丁尼生享受过此种殊荣[42]。朗费罗去世后,他的半身雕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现身。朗费罗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美国诗人[43]。
朗费罗的声名不只限于文学方面。他的诗歌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他的诗歌为歌曲、唱诗班作品、歌剧、音乐、戏剧、绘画、交响乐、盛装游行(盛会)、电影等艺术样式提供了主题。例如,《伊凡吉琳》和《乡村铁匠》都多次被改编成电影。而《海华沙之歌》不仅给美国的美术家、作曲家、卡通作家、装潢人士提供了一个流行的主题,而且给盎格鲁—非洲的作曲家塞缪尔·柯勒律治·泰勒(Samuel Coleridge Taylor)的极为流行的清唱剧提供了素材。直到“二战”时期,该剧还在一年一度的为期两周的节日中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表演,届时,几乎有一千个英国唱诗班歌手身着印第安服装进行表演。可见,《海华沙之歌》在文化领域多么流行[44]。
但是,朗费罗无疑是迄今为止美国文学史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谜。因为他在他的时代名震天下,但是现在几乎无人问津。1855年,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和惠特曼的《草叶集》(第一版)同时出版。前者的销量说明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而惠特曼却不得不将自己那些卖不出去的诗集作为礼物送人。但是,在后知后觉的美国批评家和读者发现惠特曼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诗人之后,惠特曼在美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就一直在朗费罗之上。由于现代主义的兴起,审美趣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朗费罗作品的审美风格与美国读者的欣赏趣味相去甚远,他几乎被现代读者抛弃了。
那么,在当代我们究竟该怎样定位朗费罗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呢?
朗费罗一生积极致力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1826—1836年这10年间,朗费罗两度游学欧洲,以不同于他的美国同胞的方式充实了自己:他研究欧洲语言和文学,广泛翻译了欧洲诗歌,其范围之广令人惊讶。1845年,朗费罗出版了他从十种欧洲语言翻译过来的大部头译著《欧洲诗人与诗歌》(The Poets and Poetry of Europe)。1867年,他出版了更负盛名的译著《神曲》。在朗费罗看来,把过去植根于欧洲的多种文化融合到美国文化当中,是美国文化脱离英国文化的根本策略。朗费罗通过翻译欧洲各种语言的诗歌,不仅为美国诗歌建立了一个参考系,而且试图将欧洲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美国,以实现对美国语言和文化的改造,从而为美国文学的本土化这一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朗费罗的翻译不是意译,而是直译,基本上采用了原诗原有的格律。通过翻译实践,朗费罗尝试了各种格律。他不仅运用了英语中已知的几乎每一种传统格律,而且试验了新的格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鉴赏家眼里,朗费罗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他成功地用英语创作了古典六音步诗作。朗费罗《海华沙之歌》的成功,不仅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进一步树立了他的文学权威的形象。朗费罗同时拥有欧洲的头脑和美国的智慧,兼备批评的才能和创造的活力,这些因素完美地塑造了朗费罗具有国际视野的美国学者型诗人的身份。他通过向美国译介欧洲文学,给美国诗人建立了一个文化参考的框架,即由盎格鲁—美国的文学转向整个欧洲文学传统。这一朝向欧洲模式的转变,部分来自朗费罗与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共鸣[45],更重要的原因是,朗费罗企望借此使美国文学走出英国文学的阴影,从而建立起有别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民族文学。这一切不仅对当时的诗人产生了影响,而且得到了美国现代主义诗歌领军人物艾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的回应。通过艾略特和庞德,美国诗人作为欧洲文化继承人的命运渗透到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后来的一大批诗人都将自己视为美国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媒介。由朗费罗开创并经由庞德和艾略特发扬光大的这一传统,惠及美国诗人和美国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朗费罗为建构美国民族文学付出的心血不应被历史遗忘。在当代美国学术界将朗费罗排除于美国重要作家行列之外的情况下,我们旧事重提,充分肯定这位伟大的作家为建构美国民族文学做出的重大贡献,并非不合时宜,而是体现了一种文学的良心。
在如何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的问题上,朗费罗表现出了积极的自觉意识和深切的使命感。他在大学毕业演讲《我国本土的作家》(Our Native Writers,1825)中呼吁,美国公民应该拿起笔来共同创作表达“我们民族特点”的诗歌[46]。而在他的那个时代,美国的民族性远远没有成长到足以代表美国身份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土著文化就成为确立美国民族诗歌身份的必要元素。朗费罗认为,使美国作家的作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的必要方法就是使用美国本土的素材。他在《我国本土的作家》中指出,美国作家要尽量使“每一个景点神圣化”,这样,“每一块岩石都将成为记录典故的编年史,印第安预言家的坟墓将会像古代帝王的坟墓一样更神圣”[47]。虽然印第安人的历史并不是美国人的历史,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作家看来印第安历史是美国文学重要的本土题材。这是当时美国作家和美国文学不可避免的尴尬境遇。
《海华沙之歌》是朗费罗践行他的上述两个理论主张的结果。在这部诗歌里,美国民族文学要以欧洲文学传统为参照系和美国作家要使用本土题材的两个理论主张得到了体现。朗费罗在诗歌格律方面驾轻就熟,这使他对依据所要表现的题材选择与之配适的格律这一问题保持着天才的敏感。在1854年6月22日的日记中,朗费罗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要写一首歌唱美国印第安人的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计划,唯一的计划。这首诗将要把他们的许多美丽的传说编织成一个整体。我还想到了一种韵律,我觉得这是适合于这个主题的唯一正确的韵律。”[48]这个计划的成品就是《海华沙之歌》。而朗费罗这部诗歌的素材主要来自历史学家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的著作,即《美国印第安部落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史学和统计学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History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History,Condition,and Prospects of the Indian Tribes of the United States,1851—1857)和《阿尔吉克研究》(Algic Researches,1839)。《阿尔吉克研究》收集了一组奥吉布瓦和奥塔瓦的神话与传说。而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就是以奥吉布瓦人喜爱的恶作剧者麦尼博兹霍(Manibozho)的故事为蓝本的。为了与这样的题材相适应,朗费罗从芬兰史诗《卡莱瓦拉》借来了无韵扬抑格四音步。在1855年10月29日写给T.C.Callicot的信中,朗费罗说:“在《海华沙之歌》中我为我们古老的印第安传说所做的,正如佚名的芬兰诗人为他们的古老传说所做的一样,而且我运用了同样的格律。不过,当然,我没有采用他们的任何传说。”[49]印第安题材这一标志性的美国本土题材与芬兰史诗《卡莱瓦拉》的格律等相结合,赋予《海华沙之歌》区别于英国诗歌的独创性。这一尝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霍桑指出,美国存在三大著名问题:清教徒、印第安人和独立战争[50]。当然,在美国作家中并非只有霍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印第安题材这一美国独有的题材而言,库珀已经通过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卓越的实践。那久负盛名的《皮裹腿故事集》中的杰作《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奠定了库珀“民族小说家”的地位。库珀的皮裹腿系列故事,不仅让美国东部沿海大城市里的读者心醉神迷,而且让许许多多的欧洲人了解了美国边疆生活的现实。《拓荒者》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就在英国和法国印行。不到一年时间,它就成为两家互相竞争的德国出版商的香饽饽。最后,30家德国出版商竞相推出了各种版本的《皮裹腿故事集》。在法国,也有十几家出版商争着推出库珀的作品。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埃及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到19世纪20年代末,全欧洲的孩子们都在扮演印第安人[51]。而朗费罗是更为自觉地倡导美国作家以印第安题材创造美国民族文学的作家。他的《海华沙之歌》就是以印第安人为主角的。《海华沙之歌》出版后创造了令人望尘莫及的销量。它最终成为最受欢迎的美国长篇诗歌。这部以美国土著的术语呈现美国土著的传说和习俗的诗歌,不仅被翻译成了每一种现代欧洲语言,而且被翻译成了拉丁文。这部诗歌使朗费罗成为用英语写作的最受欢迎的诗人。《海华沙之歌》被誉为“美国的第一首史诗”,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朗费罗的生花妙笔与印第安题材的完美结合。总之,印第安题材作为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文学的标志性本土题材,在建设美国民族文学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如前所述,《海华沙之歌》的主要素材来源是斯库克拉夫特收集的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等资料。通过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朗费罗不仅创造性地改造了印第安神话传说和印第安诗歌,而且借鉴了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叙事艺术和印第安诗歌的技巧。朗费罗对印第安文学口头传统的借鉴,无疑是实现诗歌创新的一个积极策略。在19世纪早期,一些美国学者与作家就意识到土著美国人的口头文学传统对建立美国民族文学具有重要价值。沃尔特·钱宁在1815年发表于《北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土著美国人的口头文学是美国真正的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吸收土著口头传统是建立美国民族文学的一条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对印第安口头传统的吸收是其自觉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的一种尝试。
在《海华沙之歌》问世以后,对它的评论可谓风起云涌。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海华沙之歌的原创性问题。有人指出,《海华沙之歌》使用的平行句法就来自芬兰史诗《卡莱瓦拉》。朗费罗对这一指责的回应是,这位批评者可能不了解使用平行句法是印第安诗歌和芬兰史诗共有的特征[52]。此类问题不一而足。朗费罗的辩词表明,《海华沙之歌》确实具有印第安口传文学的特征。而其重要价值就在于,使《海华沙之歌》具有了与英国诗歌相区别的不同寻常的特征。正因如此,朗费罗在该诗出版之前一度感到困惑不安。《海华沙之歌》于1855年3月完成,同年10月出版。朗费罗怀着极大的热情愉快地完成了该诗的创作,但是他一想到自己的读者就感到十分困惑。他曾了解过自己的朋友对该诗的看法,但是众说纷纭。在即将出版之际,他自己则有点摇摆不定。1855年6月,他表示:“我对这支歌的感觉变得越来越白痴了,而且不再知道它是好是坏。”稍后他继续写道:“我极大地怀疑《海华沙》的其中一章——不知是否该保留它。当长时间地盯着一个对象时,一个人的思想会变得多么古怪啊。”[53]事实上,在创作《海华沙之歌》之前,朗费罗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优秀诗人了,而为什么面对《海华沙之歌》他无法确定该诗是好是坏呢?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印第安口传文学因子被移植到了英语书写诗歌中,这种移植导致的创新与英语诗歌惯常的批评标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使朗费罗无法对该诗做出有把握的判断。但是,《海华沙之歌》的成功无疑就是对朗费罗所走的创新之路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朗费罗以借鉴印第安口传文学传统的方式赋予美国诗歌不同于英国诗歌的民族特色的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从诗歌题材和艺术手法等方面来考量,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在美国文学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19世纪美国民族文学的重要成果。
[1] 转引自[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一卷),蒋坚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9页。
[2] 转引自[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一卷),蒋坚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页。
[3]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页。
[4]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页。
[5]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页。
[6] [美]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上册),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页。
[7] 转引自[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8] 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曾在美国知名杂志《格雷厄姆》任职,与爱伦·坡过从甚密,坡死后,曾参与处理了坡的许多作品。
[9] 转引自[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0] 转引自[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6页。
[11]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页。
[12]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
[13]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14]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15]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16] [美]埃利奥特·埃默里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17]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一卷),蒋坚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页。
[18] [美]埃利奥特·埃默里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19] [美]埃利奥特·埃默里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20]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21]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22]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23]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页。
[24]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5] 《见闻札记》包括33篇小品文和故事,其中仅有4篇是关于美国题材的作品。
[26] [美]埃利奥特·埃默里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27]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页。
[28]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599页。
[29]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Poems and Other Writings,ed.J.D.McClatchy,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00,p.791.
[30]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Poems and Other Writings,ed.J.D.McClatchy,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00,p.792.
[31]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Poems and Other Writings,ed.J.D.McClatchy,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00,p.792.
[32]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Poems and Other Writings,ed.J.D.McClatchy,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00,pp.793-794.
[33]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Poems and Other Writings,ed.J.D.McClatchy,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00,p.794.
[34]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Poems and Other Writings,ed.J.D.McClatchy,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00,pp.794-795.
[35] 胡家峦主编:《惠特曼经典散文选》,张禹九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6] 胡家峦主编:《惠特曼经典散文选》,张禹九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37] [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6—87页。
[38] 胡家峦主编:《惠特曼经典散文选》,张禹九译,湖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39] [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6页。
[40] 王诜编:《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41] Parini Jay,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oetry,pp.64—65.
[42]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页。
[43] Parini Jay,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oetry,p.65.
[44] Parini Jay,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oetry,pp.65-66.
[45] 朗费罗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曾大力推介德国文学,歌德是其教研工作的重要对象。
[46]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
[47]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李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页。
[48] 转引自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The Song of Hiawatha;With Illustrations,Notes,and a Vocabulary and an Accountof a Visit to Hiawatha's People,by Alice M.Longfellow.Boston;New York:Houghton,Mifflin & Co.,1901,p.5。
[49] 转引自Ernest J.Moyne and Tauno F.Mustanoja,Longfellow's Song of Hiawatha and Klevala,American Literature,Vol.25,No.1(Mar.,1953),pp.87-89,Publish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
[50] [美]埃利奥特·埃默里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51] [美]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页。
[52]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The Song of Hiawatha;With Illustrations,Notes,and a Vocabulary and an Account of a Visit to Hiawatha's People,Alice M.Longfellow,p.8.
[53]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The Song of Hiawatha;With Illustrations,Notes,and a Vocabulary and an Account of a Visit to Hiawatha's People,Alice M.Longfellow,p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