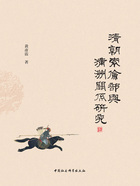
四 索伦部研究状况
国内关于索伦部的研究始于晚清边疆史地学兴起之时,散见于个人和官方著述中。魏源的《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记载清太宗收抚黑龙江北索伦部,清圣祖编设墨尔根新满洲,科尔沁蒙古献出达瑚尔壮丁。魏源写作《圣武记》,乃出于鸦片战争时事所迫,英人入侵民族危机之时。魏源时任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常年阅读内阁档案。清朝兴起和盛世的记载跃然纸上,而身处嘉道中衰的时局,目睹清朝深陷于农民起义和列强相逼的窘境,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暗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激发了魏源探索清朝盛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前代帝王处理边疆、民族、军事问题的得失,立志为救亡图存寻找办法。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中国北方边疆史地名著,也是专门研究俄罗斯史地和中俄关系的代表作品,对于清代中后期的北部边防和北疆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泽县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曾代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是西北边疆史地学代表人物。
何秋涛有感于俄罗斯对清朝的重大威胁,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出于知己知彼的考虑,博采群书,辑成《北缴汇编》6卷,后扩展为80卷。咸丰皇帝大加称赞,赐名《朔方备乘》,已显示出该书的重大实用性。全书共80卷,目录1卷,卷首12卷,列有圣训、圣藻、钦定书诸项,圣训是辑自清太宗至道光帝历朝皇帝关于北部边疆事务的上谕,中俄界务在此十分丰富。钦定诸书摘录《平定罗利方略》《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文献通考》《钦定大清会典》中有关俄罗斯及中俄关系的史料。正文68卷,其中圣武述略6卷,考24卷,传6卷,记事本末2卷,考订诸书15卷,辨正诸书5卷、表7卷、图说1卷。内容包括三北边疆的民族、山川、镇戍、地理沿革、中俄界址以及俄国的历史地理,从汉代到清代,从文献到实地,考证、校勘、训诂、订误,考据缜密、图文并茂。版本主要有咸丰十年(1860)刻本及石印本,毁于战火,后经李鸿章总督直隶,全力恢复残稿,于光绪七年(1881)再次刊行。清代翰林院编修李文田撰《朔方备乘札记》一卷,从音转上辨正山、地及人物名称,颇有价值。
《朔方备乘》卷二《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对索伦名号、影响以及索伦部兵丁在黑龙江军事力量布防中的位置。《朔方备乘》中的《平定罗刹方略》记述了罗刹对索伦的袭扰,达呼尔头目倍勒儿前往雅克萨城生擒罗刹七人。圣祖免去索伦、达呼尔一年贡赋。《朔方备乘》中的《雅克萨城考》记载巴尔达齐和博穆博果尔对满洲的不同态度及太宗征服索伦部的过程。
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从地理的角度介绍索伦、鄂伦春、达呼尔的分布。《东北边防辑要》详述鄂伦春、索伦、达呼尔之分布以及索伦部首领叶雷、博穆博果尔、巴尔达齐、根特木耳史事,清军征服索伦部诸屯及所获人口。
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卷三对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及黑龙江驻防八旗逐个梳理。英和的《卜奎纪略》记载康熙年间索伦、达呼尔南迁到嫩江流域,雍正十年驻防呼伦贝尔,乾隆年间又遭裁撤。卷五对布特哈贡貂互市制度介绍详备。
方观承的《卜奎风土记》从风俗上记述索伦、鄂伦春贡貂,以犬捕貂,鄂伦春妇女亦善骑射。
屠寄的《黑龙江舆图说》从地理角度讲述索伦、鄂伦春之分布,布特哈打牲衙门之职能,齐齐哈尔城之建立,黑龙江省河流分布。
《黑龙江城图说》详述东北民族源流、三大族系演变、黑龙江省建城驻防,墨尔根、布特哈、呼伦贝尔之民族分布、行政建置。
林佶的《全辽备考》记载索伦披甲八千,美貂称作索伦皮,满洲击退阿罗斯,保护索伦的历史。
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于疆域、建置、职官、贡赋、兵防、贸易方面研究甚详,尤其对索伦、达呼尔久居俄境,管理颇难,但其面对俄人欺凌,则保持沉默,此处最见功夫,满洲由此对索伦、达呼尔可收抚之。
长顺主编的《吉林通志》记载打虎儿、索伦从事农耕,收获甚多。对索伦并征调之后考虑其各有产业,回往原籍安置。
徐世昌主编的《东三省政略》将陈满洲、新满洲、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并列排出,可见各民族的清晰边界,也肯定了索伦三部的抗俄贡献。从建置、警务、学务、矿产展开,对兴东、呼伦贝尔收抚鄂伦春详细阐述。对黑龙江省管制、民政、财政、垦务、旗务、学务全面记载,其中涵盖索伦部诸多事务。
民国时期东北方志大肆纂修,记述更为详尽。
黄维翰的《呼兰府志》述及沿革,从交通、武事、户口方面有所记载,其历年户口考可作为研究索伦、达呼尔人口的重要资料。
徐希廉的《瑷珲县志》对满洲征调索伦部兵丁参加全国多次战争有所阐述,回部、准部、缅甸、金川各省之役无不从征。只有与八国联军作战由于档案无存,不知详情。详述索伦、达呼尔、库玛尔路鄂伦春的居址姓氏户口、征调情况、官宦人员,还附有库玛尔路鄂伦春第一初等小学校首创师生人名,徐希廉为鄂伦春人下拨荒地、建立学校,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此为鄂伦春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程廷恒的《呼伦贝尔志略》记载从雍正十年(1732)设副都统,由布特哈迁来索伦1636人、达呼尔730人、陈巴尔虎275人、鄂伦春359人,这3000人编为五十个牛录组建呼伦贝尔八旗。到光绪二十年(1894)设协领,专门负责收抚托河路鄂伦春。索伦兵已不像开国之初号称劲旅,而是有名无实,战斗力锐减。民国八年(1919)陈巴尔虎独立一部,脱离索伦,达呼尔族仍在索伦名下。附有索伦、鄂伦春七个旗的户数、人口数和男女比例。并对卓尔海、萨垒、瑚尔起、恒龄、明昌、达密兰这些索伦、达呼尔官员履历详细记录。
魏毓兰的《龙城旧闻》最有价值处为人物部分,详载海兰察、莽喀察、德兴阿、舒通额、穆图善、巴杨阿、伦布春、勒尔克善、阿兰保、由屯、沙晋、阿穆勒塔的生平事迹。
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呼伦贝尔》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对索伦、达呼尔、鄂伦春、雅库特进行研究,结合畜牧、游猎的生产生活方式,族群边界十分清晰,令人耳目一新。对呼伦贝尔的行政组织介绍明确,索伦巴尔虎左右翼各四旗及鄂伦春镶蓝旗。其职官沿革、各部分合,设置总管、副总管、骁骑校之数量,都有详细记载。
方式济的《龙沙纪略》经制篇对卜奎、墨尔根之索伦、达呼尔户口有详细记载,风俗篇对鄂伦春、索伦皆有所阐发。物产篇记述索伦马、鄂伦春鹿及桦树皮。
张伯英总纂的《黑龙江志稿》从地理、职官、人物、风俗、宗教、军事、垦务、姓氏源流、旗务、民务、物产、财务预算、学校教育、武备、交涉、征调等方面对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展开综合考察,是最为完备的一部黑龙江省志。
孟定恭的《布特哈志略》是布特哈建制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书,发行于1931年,由达斡尔族孟定恭纂修。孟定恭,族名索米子宏(汉译为“修道”),字镜双,号半园叟,西布特哈(今内蒙古自治区莫力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大莫尔登屯正白旗莫尔登氏。毕业于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蒙旗师范学校,精通满汉双语,注重收集地方民族资料,勤于实地调查。历任西布特哈笔帖式、验骑校、佐领、黑龙江省议会议员、西布特哈总管公署旗务科长、布西设治局教育局局长等职。
布特哈为满语,汉译为“打牲”。康熙二十二年(1683),布特哈打牲处行政由理藩院管理,军事统归宁古塔梅勒章京。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宜卧奇后屯设立总管衙门,改由黑龙江将军管辖。康熙三十年(1691),设达斡尔、索伦总管2员,设副都统衙总管1员总辖两部,同理藩院的满洲总管1员共驻于齐齐哈尔屯,直属理藩院。形成了军民分治的管理体制。1906年以嫩江为界将布特哈分为东、西两路布特哈。
全书分历代沿革(含民族、历任官吏姓名)、村落姓氏(含物产、礼节风俗)、人物(共85人)、古迹(含边堡、庙宇、碑铭、匾额)、歌谣、经政六部分,约3.7万字。资料丰富,取材严谨。取事实不取文艺,颇具志书之特点。《辽海丛书》(第七集)将其收录其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渤海国志长编(外九种)》将其点校,方便使用。
《布特哈志略》详述布特哈地方历代沿革,至清代以打牲音译得名,康熙朝设置总管衙门,光绪朝先设副都统,后又裁撤,划分东、西两路布特哈。对东、西布特哈村落姓氏列表统计,宗教、饮食、服饰、性格均有涉猎,所设县镇情况记载明确,后附职员列表。尤其重要人物生平甚详,如博穆博果尔、巴尔达奇、博尔奔察、海兰察、由屯、阿那保、都兴阿、西凌阿、色楞额、长顺等名将。
《清代方略全书》[50]是记载清朝军事活动的实录。有些方略详细记载了索伦兵参战情况。
温达等撰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是《清代方略全书》之一种,四十八卷,66万字。康熙四十七年(1708)武英殿刻本,《四库珍本丛书》也将其收录。另有满文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单行本。卷首圣祖亲撰《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一卷和温达奏进的《方略表》。卷末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文》《勒铭察罕七罗碑文》《勒铭拖诺山碑文》《勒铭昭木多碑文》《勒铭狼居胥山碑文》。
内容为圣祖平定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之方略。康熙十六年(1677)六月噶尔丹奉表入贡及饬令与喀尔喀修好,但噶尔丹迅速膨胀,攻占吐鲁番和哈密,势力扩张至甘州。康熙十九年(1680)噶尔丹出兵南疆,以12万铁骑攻占叶尔羌与喀什噶尔,扶植“白山派”首领和卓伊达雅图上台,称“阿伯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与其子统治南疆,皆听命于噶尔丹,断绝与清朝的关系,直至乾隆时彻底消灭准部,清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噶尔丹兼并南疆后,又挥师西向,在四年间,接连打败哈萨克、诺盖(居黑海沿岸)、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抵抗,建立了准噶尔的军事统治。康熙二十三年(1684),已控制了西北地区,北达鄂木河,西至至于巴尔喀什湖以南,东至鄂毕河的中亚地带,力量达到卫藏。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三部被攻占。康熙二十九年(1690),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与清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圣祖三次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之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昭莫多之战,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第三次亲征噶尔丹。马思哈、费扬古两路进兵,噶尔丹余部纷纷出降。三月噶尔丹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毒药而死,其重建大蒙古国的梦想终于告灭了。圣祖三征噶尔丹,扬威西北,平定准噶尔叛乱,保蒙古、卫京师,八年浴血战斗以全胜而告终。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献噶尔丹尸首。该书中有大量圣祖赐予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的上谕原文,可补《实录》未载之失。
傅恒等撰的《平定准噶尔方略》是《清代方略全书》之一种,清朱丝栏抄本,体量庞大,分为三编,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2卷,共171卷,纪略1卷。卷首傅恒等撰《恭进平定准噶尔方略表》。
前编上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七月,下迨于乾隆十七年(1752)九月。记载圣祖三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和策旺阿拉布坦。策旺阿拉布坦派人杀死拉藏汗,占领西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禵击败大策零敦多布,驱逐准噶尔军出西藏。雍正二年(1724)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病故,其长子噶尔丹策零继承统治权。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病死。直至准噶尔部名将大敦多卜策零之孙达瓦齐杀噶尔丹策零长子喇嘛达尔扎而自立。
正编八十五卷,上起乾隆十八年(1753)十月,下迨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平定伊犁,俘获达瓦齐。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南疆大小和卓木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叛乱。自此历经康雍乾三朝终于统一西北边疆。
续编三十二卷,上起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月,下迨于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记载高宗设立伊犁将军,任用流官,驻防城镇。移民屯田,以作屏藩,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过程。
保泰等撰的《平定廓尔喀纪略》是《清代方略全书》之一种,五十四卷。卷首四卷,前三卷为高宗歌咏战争的御制诗,第四卷为高宗御制文,包括《十全记》《喇嘛说》《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乾隆六十年编刊,殿版印行。与《巴勒布纪略》形成姊妹篇,分别叙述高宗两次用兵西藏,驱逐廓尔喀之事。《平定廓尔喀纪略》上起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下迨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记载高宗第二次用兵后藏、追击廓尔喀侵略军和处理善后事宜。该书内容翔实,比《卫藏通志》《清高宗实录》更加具体。清朝钦差大臣巴忠在第一次西藏与廓尔喀的战争中,私自议和,承诺用每年300个银元宝换回廓尔喀已占土地。未得到达赖喇嘛的允许,次年无法兑现。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福康安、海兰察率军1.4万人入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将廓尔喀军队驱逐出境,福康安率军5000人追入廓尔喀国内。七月,廓尔喀投降,高宗准许。廓尔喀交出所抢财宝,交出与西藏私立的协约。高宗改革西藏政治体制,驻藏大臣总揽藏务,监督权完全转变为行政权。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创设金瓶掣签制,控制灵通转世。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范围。平定廓尔喀对于巩固西南边疆,统一清朝版图具有重要作用。虽有人认为劳而伤民,但从长时段来看,益显其珍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点校版,质量很高。
托津等撰的《平定三省教匪纪略》是之一种,四十二卷,卷首一卷。托津、董诰、张煦、英和、卢荫溥等撰,嘉庆年间刻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告成,与《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为姊妹篇。清兵入关统治中国以来,历经顺、康、雍、乾四朝,凭借文治武功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接续中国传统王朝之正统。康、雍、乾三帝屡兴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以巩固统治。但是民间反清复明的浪潮此起彼伏,往往借助秘密社会民间宗教起事。该书记载自乾隆中期以来,天地会、白莲教在南北各地活跃起来。如安徽刘松带领其子和两个弟子在川楚陕甘收徒传白莲教,谪戍伊犁。乾隆末年川楚陕白莲教已成不可抑制之势,国本动摇。嘉庆元年(1796)湖北张正谟、聂杰人发动起义,拉开了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响应,加上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清政府应接不暇。嘉庆九年(1804)九月,历时八年半,清政府才平定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林清率领200 名教徒袭击紫禁城。康乾盛世,盛极而衰,嘉庆时期正是清朝由盛世走向中衰的转折点。清政府调集16省军队平定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五省40多万人的白莲教大起义,耗费白银2亿两,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社会动乱剧烈。进入道光时期,变乱频发,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并起,列强入侵,国门洞开。
《黑龙江通省事宜》将呼伦贝尔、布特哈职官设置与俸银逐个排列,很有价值。
张国淦的《黑龙江志略》记述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即鄂伦春类),黑龙江各城地理职官、山脉水系。
缪学贤的《黑龙江》记载索伦、鄂伦春之战事,伊犁、卫藏、平捻豫东、吉林马贼,海兰察依仗军功崛起。光绪朝清廷收笼鄂伦春,因管理松散,鄂伦春人有跟沙俄交易貂皮者,并潜入沙俄境内,成为俄籍。
郭博勒氏是清朝达斡尔族十八个哈拉中,四个最大的哈拉之一,高官辈出,子弟繁盛,著名的有阿那保、都兴阿、西凌阿、穆腾阿,郭博勒氏家谱在东北民族中非常珍贵,记录了家族数百年十余代的历史。郭克兴在民国肇始着手编撰家谱,《黑水郭氏家谱》共有八种,分别是《乡土录》《世系录》《世德录》《扬芬录》《先茔录》《旧闻录》《艺文录》《济美录》。
《黑龙江乡土录》体例独特,将众多乡土文献按照方舆和部族分列,十分少见,却很方便读者查找。部族志中对达呼尔、索伦、鄂伦春之源流分列各种方志之观点,对近代人物的官职、军事活动、赏恤、事迹、著述列表呈现,并对达斡尔族精英有所评论,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博穆博果尔、巴尔达齐、齐三、高喀鼐均给予肯定,对乾隆朝以后达斡尔族军功卓著,但精英大多认同满洲统治,却很少顾及家乡,致使沙俄入侵,族人南迁,丧失江北,感慨万千。号召清末族人从教育起步,自觉自强自存。《黑水郭氏世系录》中述及《郭博勒姓氏考》,对家族源流、同宗各姓详加考订。《黑水郭氏扬芬录》以郭克兴之父穆腾阿为中心人物,主要叙述其平粤、平捻、平回、平枭,驻防江宁,武功卓著。《黑水郭氏旧闻录》将家庙、宅第、祠宇、庄田、金石、文字、图像等遗迹,尽行收录,可作为社会史材料加以运用。《黑水郭氏世德录》分为近支碑传和远支碑传,辑取诸多传记材料,对研究者来说节省很多时间。
黄维翰的《黑水先民传》清传共24卷,其中众多人物传记是涉及索伦部精英的,如博穆博果尔、巴尔达齐、根特木耳、海兰察、穆腾阿、由屯、阿克岛、倍勒尔、鄂博什、阿满泰、纶布春、阿那保、色尔衮[51]、西凌阿、明庆、德兴阿、都兴阿、多隆阿、恒龄、舒通额、安住、花尚阿、穆图善、依楞额、色楞额、长顺、奇三、 绰尔图、努固德等非常系统,史事完备,可作个案研究。
绰尔图、努固德等非常系统,史事完备,可作个案研究。
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是一部著名的东北史地著作。作者是来自清代吴江(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的流人,字南荣,小字苏还,著名流人、诗人吴兆骞之子。吴振臣康熙三年(1664)生于宁古塔,康熙二十年(1681)随父离开东北,结束流人生涯。该书成于康熙六十年(1721),共一卷,近九千字,是吴振臣晚年的回忆录,原汁原味回忆了其亲身经历,内容包括宁古塔的山川名胜、风土人情和土特物产,以及其父流放经历、沙俄入侵、边疆防务,还有南归所经驿站里程。其父吴兆骞诗作颇多,广为传颂,并被宁古塔将军巴海聘为书记,教其二子,可见流人对东北地区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关于沙俄入侵宁古塔及防戍情况的记录,是东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史料。山川名胜、风土人情、土特物产反映了当时东北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真实面貌。南北炕、萨满跳神、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是东北少数民族的标志性社会生活文化。该书版本众多,有道光十年长沙顾氏刊《赐砚堂丛书新编》本,道光间刊《昭代丛书》本,道光二十三年郑氏青玉房刊《舟车所事》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龙江三纪》点校本方便实用。另外《辽海丛书续编》第2册也将其收录进去。
方式济的《龙沙纪略》是一部著名的东北史地著作,作者为清代来自安徽桐城的流人,字屋源,号沃园。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授内阁中书。方式济曾祖方拱乾、祖方孝标、父方登峄四代流人,青史留名。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由于其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氏族人继顺治朝南闱科场案方拱乾及其子流放东北后,再次受到牵连,方登峄和方式济共四人贬谪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城。方式济家学渊源,工诗善画,流放黑龙江期间,考察古迹,遍访多方,结合找到的历史文献,写出了《龙沙纪略》。该书分门别类,共为九目,一方隅、二山川、三经制、四时令、五风俗、六饮食、七贡赋、八物产、九屋宇,是研究清代前期东北地区沿革地理、社会风俗、对俄关系的重要文献,具有开创之功。东北地名多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于关内人来说很陌生,故了解其行政建制尤为困难。在《方隅》目中,将东北三将军的辖区范围、治所迁移明确阐述。东北平原山水相连,河流交错,源流复杂,在《山川》目中,皆做了详细记载。尤其对黑龙江之源的记载十分详备。在《经制》目中,对黑龙江境内驿站设置、驿路线路记载明确,还有关于中俄两国的界务事宜。该书版本众多,最早的是有乾隆二十年(1755)桐城方氏刻的《述本堂诗集》本。道光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颇为著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龙江三纪》点校本方便实用。另外《辽海丛书续编》第2册也将其收录进去。
《山中闻见录》是明代遗民彭孙贻所撰,记载明清战争的史书,作者原署名为管葛山人。彭孙贻字仲谋,又字羿仁,号茗斋,浙江海盐武原镇(今浙江省海盐市)人,明末拔贡生。明亡后,终身不仕清,闭门写作明末史事,也有大量诗词问世。其史观崇明蔑清,严守华夷之辨,其著作为清朝禁书。其父彭观民为南明隆武朝太常寺少卿,在江南抗清战争中于赣州保卫战殉难。该书共11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6卷,记载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反明、以“七大恨” 誓师出兵,首战抚顺,取得萨尔浒大捷,建州女真勃兴建国。皇太极使用反间计害死袁崇焕,统一漠南蒙古,收降三顺王,组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入口作战,决战松锦。多尔衮率清军挥师入关的历史。第二部分为第7卷,内容为《戚继光传》《李成梁传》《徐从治传》《刘綎传》《杜松传》,歌颂这五位明朝将领维护统一,保卫边疆的英勇事迹。第三部分为第8—11卷,内容为《西人志》《东人志(女真考)》《东人志(海西)》《东人志(建州)》,叙述了元末以来的明朝与蒙古瓦剌部、鞑靼部史事,上古以来的女真源流、分化整合及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的过程。该书脉络清晰,史实准确,但由于在清朝为禁书,没有公开的刻本。罗振玉根据钞本将该书刻印刊行,收入《玉简斋丛书》,其中第3—5卷佚失,现在看到的第3—5卷为后人伪作。
《东三省舆地图说》,1卷,是曹廷杰关于东北历史地理、民族、考古方面的学术札记。曹廷杰(1850—1926),字彝卿,湖北枝江人。同治十三年(1874)入北京国史馆,做汉誊录。光绪九年(1883)来到吉林,在靖边军后路营中办理边务文案。历任吉林边务文案总理、呼兰木税局总理、吉林知府、吉林劝业道道员、代理蒙务处协理等职。著有《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前者侧重于历史文献的搜集研究,后者侧重于实地调查分析。《东三省舆地图说》综合了前两本书的特点,将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综合考证分析。光绪十一年(1885)曹廷杰奉派考察吉林、黑龙江两省与沙俄边界。绘成《简明图说》,后经补充,并附以作者关于东三省的条陈十六条,光绪十三年(1887)此书刊行。该书正文53条,从“肃慎国考”到“中俄东边界段说”,时间跨越几千年。内容包括民族分布、行政区划、地名、交通水道、碑文等。突出贡献是其对明代奴尔干都司永宁寺碑的碑文研究,通过明朝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尔干海及东海苦夷事,证明《明实录》《明会典》记载的东北卫所之正确性,从而说明明朝的统治力量已经实际到达了奴尔干都司。该书收入《皇朝藩属舆地丛书》,《辽海丛书》(第七集)也将其收录其中。
当代学术成果数量众多,经过梳理,现将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分析如下。至于大量的期刊论文将在正文中,分专题加以讨论。
杨茂盛的《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提出宗族部族的概念,认为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不能直接形成民族和国家,二者之间必须经过宗族部族阶段,这个阶段形成的标志是宗族的统治阶级率先“立宗命氏”、群体兴起民族意识,继而形成部族。[52]鄂温克族的家长奴隶制是在毛哄的基础上形成的。[53]由于清朝的介入,即将瓦解的氏族组织被编为牛录,在八旗制的庇护下,鄂温克人经过有序的发展,依附于满洲贵族,不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了。
秋浦的《鄂伦春社会的发展》[54]是关于鄂伦春族研究较早的著作。该书的观点比较传统,认为个体家庭、乌力楞(家庭公社)、氏族三足鼎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血缘纽带关系的解体,鄂伦春人经营农业遭受了失败,在清代布特哈八旗的“摩凌阿鄂伦春”在满洲贵族的主导下频繁征调参战,五路“雅发罕鄂伦春”对路的建制更加认同。路下设佐,佐这种组织形式后来发展为八旗制度,打破了鄂伦春人原有的氏族制度。在莫昆达和佐领管辖下,地域组织取代了血缘组织,个体交换取代了集体交换,私有制产生了。个体家庭脱离了氏族的控制,阶级社会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氏族制度结束了,乌力楞被地域组织代替。
赵复兴的《鄂伦春族游猎文化》[55]以游猎文化为主线,对鄂伦春族的组织形式、生产交换、宗教信仰、婚丧礼仪作了全方位的研究。都永浩的《鄂伦春族 游猎·定居·发展》[56]以鄂伦春民族的形成、发展、结构、游猎文化为主线,对清代和民国时期鄂伦春族的发展做了详尽的论述。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57]以当代鄂伦春族研究为重点,兼及黑龙江鄂伦春族的历史和社会组织。
秋浦等的《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58]是对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雅库特)的调查研究,兼及其他部分的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调查资料。跟农业区和牧业区的鄂温克人不同,游猎在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社会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时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但其内部不是一成不变,晚清时期枪支的输入使得个体家庭冲击了乌力楞(家庭公社),私有制出现了,但是很微弱,没有出现剥削现象。雅库特与鄂伦春互称“特格”,既关系密切,又有着清晰的民族边界。清代雅库特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晚清时期乌力楞(家庭公社)和个体家庭并存。
孔繁志对敖鲁古雅的使鹿鄂温克(雅库特)的研究值得关注。《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59]和《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文化变迁》[60]两书是姊妹篇。前者从历史的视角详述沿革,后者从文化的视角注重民俗变迁。
敖鲁古雅的使鹿鄂温克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三次定居,分别是1957年、1965年和2003年。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61]对2003年第三次定居做了人类学考察,这次生态移民使得使鹿鄂温克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狩猎经济转为城镇定居。然而猎民并不满意,在敖鲁古雅的使鹿鄂温克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该书从文化差异的视角研究定居对游猎民族的影响,结论是敖鲁古雅的使鹿鄂温克生活环境不像媒体宣传得那样差,相对于保人的政策,保文化则更加合适。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保留边缘族群的文化为原则。
波·少布的《黑龙江鄂温克族》[62]对黑龙江鄂温克族的族称族源、历史建制、社会组织条分缕析,书中的表格统计下了很大功夫,对于清朝鄂温克族与满洲的关系、降服人口、朝贡、索伦兵驻防征调有很大参考价值。沈斌华、高建纲的《中国鄂温克族人口》[63]是人口学的专著,从人口学的研究范式切入,很有启发。鄂温克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实行氏族外婚制,同姓不允许通婚,包办婚姻和早婚十分普遍。这些现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所改变,同姓通婚,婚姻自由,初婚年龄提高。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通婚的历史悠久,在城镇、牧区与半农半牧区两族通婚广泛,比例较高。在牧区鄂温克族与蒙古族通婚为主,在猎区与半农半猎区鄂温克族与汉族通婚为主。
吴守贵对鄂温克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鄂温克人》[64]、《鄂温克族社会历史》[65]和《鄂温克历史文化发展史》[66]这三部曲当中。三本书将鄂温克族的历史进程概括为两条主线和三个发展阶段,较为清晰。两条主线是狩猎经济和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是使用弓箭,实现以猎为主;使用动物,驯鹿驯养业出现;养殖业和种植业兴起,向生产性经济发展。
研究达斡尔族的成果最多,景爱先生的《达斡尔族论著提要》[67]是从目录学的角度出发,对清末以来关于达斡尔族研究的重要成果逐个加以评论。有几部专著值得加以强调。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68]一书,虽然在民族识别中,云南契丹后裔15万人并没有确定为达斡尔族,但是确定其来源是元代初期契丹人南征大理而镇抚于此。郭布勒·巴尔登的《新疆达斡尔族》[69]详述达斡尔人西迁、逃亡、返回与建营,八旗索伦营的行政建置,社会组织。刘金明的《黑龙江达斡尔族》[70]历史部分仅占三分之一,该书将根特木耳划为达斡尔族是错误的,应为使马鄂温克人(通古斯)。沈斌华、高建纲的《中国达斡尔族人口》[71]是人口学的专著,从人口学的研究范式切入,很有创新。达斡尔族族外通婚很常见,最多的是与鄂温克族通婚,在通婚中能够分清楚哈拉的不同,说明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的民族边界依然清晰和民族认同依然强烈。丁石庆的《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72]提出清朝达斡尔族与满洲的关系分为冲突、缓和、影响三个阶段,从达斡尔语和满语的关系上透视出两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满洲作为发展水平高的民族进入达斡尔族中,助推了达斡尔文明的脚步。达斡尔族重视教育,使用满文创作书写,最终形成了达斡尔人的达满双语文化现象。
滕绍箴、苏都尔·董瑛的《达斡尔族文化研究》[73]是当前达斡尔族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以民族认同取代民族同化,明确反对亚洲大陆二元文化对立观,驳斥新清史是“骑马征服王朝论”的变态和翻版,坚持满洲人的中国认同,清朝皇帝跟历代王朝皇帝一样,都是以儒家思想治国理政,绝非利用。倡导民族关系史的主流是和,达斡尔族跟中华各民族一样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女真与汉人的认同是在自然状态下的认同,不是强制认同。达斡尔族文化兼具农业文化和打牲文化,是东北民族中先进的代表,这源于契丹文化的优秀。作者考据精湛,确定巴尔达齐所娶的公主是努尔哈赤之弟多罗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第四子、功封固山襄敏贝子务达海之女[74],并根据乾隆年间的两位达斡尔将领托尔托保和博斌以族为氏,确定达斡尔氏是博穆博果尔的家族,因此确定博穆博果尔的族属为达斡尔族。[75]
景鄂海、巴图宝音编著的《中国达斡尔族史话》[76]和孟志东主编的《中国达斡尔族通史》[77]是新世纪以来的两部达斡尔族通史,撰写体例很相似,都是从契丹史、辽史写到达斡尔史,这一体例遭到了景爱的批评,达斡尔不能等同于契丹,他还有契丹以外的成分。民族的形成过程很漫长,不同成分出出进进不可能避免,因此不能人为地拉长本民族的历史。
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78]为民族学经典之作,作者利用西伯利亚和东北地区的调查资料系统研究了鄂温克、鄂伦春人的地理环境、经济类型、组织结构、风俗习惯等。但是作者的意识形态存在严重问题,他是站在沙皇俄国的立场,为俄国资产阶级侵略我国服务,其白俄的身份,也极力反对苏联红色政权。该书认为鄂温克和鄂伦春人是自愿接受沙俄统治,将殖民侵略描述成是发展水平高的民族对发展水平低的民族的经济帮助,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在历史观上,他认为民族(ethnos)是个认同的群体,忽视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只强调民族关系的影响,从而不可能对鄂温克、鄂伦春人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全盘的拆析。
总之,学术研究的过程,通常是从个别问题研究开始,最后上升为综合研究,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就本书而言,前人虽然在微观层面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没有在整体上研究清朝索伦部与满洲的关系,本书即要在整体上进行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注重索伦部的民族分化过程、民族意识的变迁,说明索伦部既依附满洲又具有本民族认同的复杂关系,进而找到民族之间互动交融的特点和规律,正确理解清朝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于索伦部中的三个民族的分化过程和民族意识的研究,探究满洲对其民族分化过程和民族意识的影响,是个崭新的课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民族学、社会学原理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也是个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