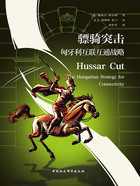
四 西方价值观的“内部侵蚀”
前文概述了西方大国忽视现存国际秩序规则的数个场景,这些事件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专家米尔斯海默曾就现实主议和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阐述发表过见解。他指出,以暴力乃至军事手段强行推广西方理念的做法,不仅让伊拉克、阿富汗等国陷入混乱,实际也未能真正促进西方价值观的传播。61更糟的是,这些干预最终导致的是西方价值观在西方国家内部受到侵蚀。62这种困境背后的原因机制如下:不惜以战争为代价,传播西方思想;西方模式的国家发现自身卷入越来越多的军事冲突,而这些军事行动在本土引发越来越多的反抗,反战的声音越发强烈。当局越来越将这些反战声音视为敌人,并开始限制那些支持这种观点的人的自由,包括他们的言论自由。63

图1-4 得克萨斯州反战示威
资料来源:盖蒂图片社
此描述囊括了具体、清晰可辨的过程。然而,我们深信这些过程指向了更为深刻的现象。64弗朗西斯·福山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不谋而合。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还写道,对原本胜利的自由民主制度而言,只剩下一个威胁,即对自身价值观的不确定性。65这种不确定性根源于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与权利扩张实践(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种实践的不当过度应用最终会导致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对根本的社群价值产生怀疑。米尔斯海默似乎也在描述这样一个过程,且两位理论家一致认为,这一过程破坏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社群组织力量,并使社会分崩离析。66
奇怪的是,正是自由主义更具批判眼光的观察者们(这超越了自由主义国际层面的局限),最早察觉到这一思想中隐藏的相对主义倾向。德国宪法法官和法律哲学家恩斯特·沃尔夫冈·博肯弗德(Ernst Wolfgang Böckenförde)指出,现代自由世俗国家在其自身无法把握的基础之上运行。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提供的自由是来自公民的内心,来自个体的道德感知,并通过同质的社会在内部进行调整时,才能称其为自由国家。另外,它本身不能试图通过法律胁迫和权威命令的手段来确保这些内部调节力量有效运行,因为这将侵犯自由原则。因此,现代世俗国家不得不向前现代的传统社会继承这些内部调节力量。67若我们认同博肯弗德的判断,即现代自由世俗国家无法复制其赖以生存的价值观,那么就不难看出,社会或政治模式生存所必需的价值观最终将受到侵蚀。68这是因为个人对社会公认价值观的接受度为社会运转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个体公民为社会利益作出了某些牺牲,因为他们认同并重视这些价值观。因此,共同价值观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共享价值观消失将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自我主张本身将判定行为对错与否,而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反而变得难以理解。西方社会中不断加剧的物质不平等程度就反映了此现象。69不平等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凝聚力,同时破坏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条件。70
因此,西方世界带来的世界秩序危机并非仅受外部因素(如挑战者日益强大)的影响。西方自身价值观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价值观传播所固有的矛盾,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霸权国家很少会保持仁慈。71
注释
1.见马扎尔(Mazarr)等人的著作(Mazarr et al.,2016)。
2.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针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恰当且易于理解的总结,他不仅关注到“世界秩序”一词在西方文明的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解释,而且还关注到该词在其他文明,如中国或伊斯兰世界,含义也不尽相同(Kissinger,2014a)。
3.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权力关系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地缘政治因素。
4.有关规范性规则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施密特(Schmidt)等人著作(Schmidt-Williams,2023; Gorobets,2020; Jovanović,2019; Shelton,2006)。
5.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可能会产生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这些行为者的崛起可能会限制个别国家行为者的主权。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规范体系,明确规定这些非国家行为者的权利和责任(Ben-Ari,2012)。
6.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有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巴里·布赞(Barry Buzan)、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巴里·波森(Barry Posen)、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
7.米尔斯海默引用了几项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Carr,1962; Gilpin,1996; Mearsheimer,2005a; Mearsheimer,2005b)。
8.其原因在于,现实主义者并不以在世界上传播他们的思想为目标,而有使命感的理想主义者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特定国家政治体系,甚至不惜以战争为代价(Mearsheimer,2022)。
9.最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包括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Nye)、安德鲁·莫拉夫席克(Andrew Moravcsik)、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
10.这种信念可以追溯至伊曼努尔·康德(Kant,2016)。康德在他的作品《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中认为,民主国家永远不会相互开战,而是在制度框架内解决冲突。这一观点构成了现代自由学派的基础,即通过夯实国际机构效力,将解决冲突限制在制度框架之内。康德的思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渗透在民主输出的观念中,依据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民主输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远非和平进程。
11.最重要的建构主义作家:凯瑟琳·西金克(Kathryn Sikkink)、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伊丽莎白·基尔(Elizabeth Kier)、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 more)以及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2.Wendt,1999.
13.伊肯伯里(Ikenberry)和卡根(Kagan)等。追随这些学者,一些匈牙利作家也认为,美国霸权主义只能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例外。即本质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能够如此强大,毫无敌手,以至于能够奉行纯粹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旨在按照符合其内部价值的利益来传播自由主义秩序”是一种例外。同时,这两位作者坚信,这样一个常规之外的国家不会走得久远(Ikenberry,2012;Kagan,2012)。
14.福山指出,自由民主不仅无可替代,这种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也将在越来越多国家中得到采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自由主义革命的显著世界特征才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进一步证明,有一个基本进程在起作用,它决定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演进模式,类似于人类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发展的世界史”。这场“自由主义革命”认为历史进程是理性的,可在理性基础上被理解,如果采用最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理性上是非西方国家的最佳选择,那么相当一部分国家都会这样做。福山只是众多宣称西方世界将取得最终胜利的众多作者之一,提出类似观点的作者还包括克劳特默(Krauthammer)、穆拉夫奇克(Muravchik)、伊肯伯里(Ikenberry)、卡根·皮科内(Kagan-Piccone)以及贝克利·布兰兹(BeckleyBrands)。
15.我们已经在《匈牙利的战略之道》(The Hungarian Way of Strategy)中讨论过这个主题: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中,人们就国际系统单极化这一议题讨论不断。讨论主要围绕单极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的持久性,究竟是将维持数十年,还是终将走向倒台?讨论最终形成三大立场。早在1990年,即苏联即将走向解体前夕,查尔斯·克劳特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中与预测多极世界秩序崛起的阵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他与带有传奇色彩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之间的辩论。保罗在其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曾预言,一个永久稳定的多极世界秩序将在20年内出现。相比之下,在克劳特哈默看来,冷战后世界体系将以单极化为特征。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将仅剩一个超级大国,即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日本、德国等次级强国。美国将有资格宣称自己为国际霸权超级大国,因为只有美国同时拥有足够强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甚至克劳特哈默也承认,美国的霸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他认为多极世界秩序要在几十年后才会出现(Krauthammer,1990)。1993年,新现实主义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即使西方联盟体系中几个国家已变得更为强大,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不会被撼动。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会采取何种战略?是采取一种孤立主义,允许其他国家在积极参与塑造国际体系的同时获得相当大的自由,还是会将手伸得更长?(Waltz,1993)。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华尔兹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确实呈现单极化,但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体系,不久后就走向终结。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了太多的任务,而没有其他力量来对抗美国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对单极化体系忧心忡忡的国家正试图增强自身实力,独立的或是作为联盟体系的一部分与美国相抗衡(Waltz,2000)。作为对新现实主义者的反驳,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对单极国际体系进行了自由化解读。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说法,美国可以采取一种策略,让潜在挑战者愿意维护该单极体系,以此达到维持单极国际体系的目的。换言之,有必要说服其他国家,相较于构建其他替代性体系与美国霸权相抗衡,维持现有的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组织益处更多。更粗略地说,世界单极化部分基于美国实力,部分基于平等参与的假象(Ikenberry,1998)。
16.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或一种有意识的决定,而是一种西方文化内在逻辑的结果。凭着一种近乎为自然法则的力量,西方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17.Plehwe-Mirowski,2009; Peck,2010.
18.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其表述为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因为在优先推动自由竞争的同时,实际促进了垄断的形成。另一方面,他建议国家应把加强竞争作为关键任务(Friedman,1951)。
19.大卫·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泰德·盖布勒(Ted Gaebler)从广义角度强调了该经济政策的几个特征:政府以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其竞争力为核心任务,采取市场为本、消费者为中心、富有创业精神的策略(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同时实行分权管理(Denhardt,2008)。
20.该原则早在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的就职演说中就已显现。总统里根对美国人民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的管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政府的管理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时常误认为,社会过于复杂,已经无法凭借自治方式加以管理,而由杰出人物所引领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高明。现在,为了不引起误解,我表示,我无意废除政府,而是要它发挥作用——与我们合作,而非凌驾于我们之上,与我们并肩作战,而非骑在我们背上。政府能够且必须提供机会,而非将其扼杀于摇篮中;促进生产,而非束缚生产。”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4年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在上任时就有一个意图:改变英国,从一个依赖型社会转变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社会,从‘拿来给我’转向‘自己动手’,从‘坐以待毙’转为‘起而行之’。”这两篇演讲都清楚地表明了该经济哲学与20世纪初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有何不同。前者中,国家职能颇丰,核心在于创造机会以及维持公平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位英语国家政治家的思想中,该原则如何与保守主义思想交织在了一起。里根和撒切尔都追求完全实现形式的自由竞争,旨在助力于那些自给自足的个人,他们靠工作生活,并为自身负责。里根的话语中,我们感受到的独特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保守主义主题。里根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等同于精英官僚机构。然而,其能否实现保守主义者的希望,还绝非确定。事实上,情况似乎恰恰相反。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回忆起,在20世纪80年代,他了解到撒切尔领导下的经济原则,但即使在那时,也能看到其缺陷。斯克鲁顿认为,当时这两位伟大的英语国家保守派领导人没有认识到,他们所信奉、优于管理式、官僚式政府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大公司和跨国公司与保守派热衷于批评的政府部门一样,都是按照完全相同的管理方式、官僚主义原则,以同样精英方式、采用同样的中央计划来运营的(Scruton,2023)。事实上,今天很少有像跨国公司这样的技术官僚实体。如果(广义上)翻拍一部反映里根时代晚期精髓的电影,即梅兰妮·格里菲斯(Melanie Griffith)主演的电影《打工女郎》(Working Girl),女主角将无法像电影中所述那般,凭借其卓越的商业理念在职场步步高升,而是通过优化Excel表的处理,从而使她的职称可以从“会计师”升为“主题专家”。
21.杰米·佩克(Jamie Peck)将20世纪90年代称为该主义的“推出”阶段(Peck,2003)。
22.布雷顿森林机构旨在促进华盛顿共识建议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传播(Phillips,2020)。
23.华盛顿共识核心在于采用以下原则:预算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削减公共开支,税收制度革新,利率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优先保护财产权(Phillips,2020)。通过西方经济治理原则的实施,西方机构实际上推动了福山采用西方模式的预测或期望的实现。
24.通过规定采纳西方经济治理原则,西方机构实际上实现了福山对采纳西方模式的预期。
25.Steger-Roy,2010.
26.治理(法语:gouvernementalité)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于1978年和1979年在法兰西学院举行的一系列讲座中提出。
27.曼弗雷德·B.斯蒂格(Manfred B.Steger)和拉维·K.罗伊(Ravi K.Roy)从概念上将新自由主义概括为一种已经成为全球化组织原则的意识形态:“例如,其中一个主张表示,建立全球一体化市场是一个理性过程,能够推动个人自由和世界物质进步。这里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和消费主义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们吸引了所有(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不受他们的社会背景影响。即使有鲜明的文化差异,也不应被视为建立单一的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市场的障碍。与之相关的一个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市场一体化终将惠及所有人,实现物质福祉的提升。这一主张旨在增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吸引力,因为它试图向人们保证,创建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将使整个地区摆脱贫困”(Steger-Roy,2010)。
28.民主和平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兴起,其灵感源自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文章《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康德表示,如果所有国家都过渡到共和宪政制度,签署和平条约,建立必要的国际法框架,采取某种国际宪法的形式,就可以实现永久和平。民主和平概念的现代倡导者包括多伊尔(Doyle)和拉塞特(Russet)。
29.例如,考虑一下华盛顿共识机构提供的发展资源如何与具体的政策措施相关联。
30.特朗普当选总统标志着所谓的杰克逊式外交政策的回归,其主要目标是捍卫和保护共和主义美德,最重要的是捍卫和保护自己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福祉和幸福,而非像自由国际主义那样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因此,“美国优先”外交策略本质上是单边战略,由此引起了联盟体系层面对北约的怀疑,并促使美国总统期望所有国防联盟成员国履行军事开支义务(Clarke-Ricketts,2017)。“特朗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反对自由秩序(基于联盟、开放的全球经济、规则制度的主导地位以及民主和人权的传播)的总统。”布兰德(Brands,2021)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尽管美方常有人表示,现实主义者在过去十年中再度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但《国家利益》主编罗亚(Roa)表示,情况远非如此(Brands,2021)。美国的现实主义思想有着数百年的传统,无数实例证明,美国能够正确评估自己的机会和能力,选择正确战术,从而维护国家利益。所有这一切都与国家自我形象紧密相连,民主输出或后来的华盛顿共识皆是如此(Roa ,2023)。然而,在过去十年中,现实主义者未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选择性地忽视美国正在与无数的内部经济、制度和政治问题作斗争,也未能正视其相对实力不再足以维持其霸权这一事实。这样一来,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往往与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同流合污(Kirschner,2008;Daalder-Lindsay,2003:288; Feulner,1996)。
31.对“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概念的任何讨论,往往不可避免地引向经典问题:“罗马人曾对我们做了什么?”或说,至少许多人喜欢用罗马来与美国类比。罗马和平(Pax Romana)指的是罗马帝国作为霸权国,在长达两百年间,主导国际秩序规则和运作原则的时期。罗马文明的压倒力量也意味着罗马世界的特点是相对和平和经济繁荣。相应地,“美式和平”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霸权,全球化按照华盛顿共识运作,由此带来相对繁荣、自由的国际秩序,包括美国凭借在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维持着全球力量平衡(Bender,2003)。关于Pax Americana的进一步解释,详见Brzezinski,1997; Nye,1990; Cox,2005; Ferguson,2005;Kennedy,1989。
32.奈尔(Nair)提请人们注意国际体系的五大变化,每次变化都导致了西方相对力量的削弱,从而对其大国地位构成了挑战。第一,世界历史的解释权已不再是西方叙事的独占领域。非西方世界的叙事现在在学术层面已牢固确立,而非西方历史观也在影响着政治行动和自信。第二,权力平衡被打破,非西方世界已积聚足够的力量来与西方地缘政治压力相抗衡。第三,西方公信力大不如前。近几十年来,它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和平倡议,而与此同时,8个“民主”国家已经向124个国家出售了武器,其中74个国家甚至在供应商国家的评估中也不符合“自由和民主”的条件(Hartman-Béraud-Sudreau,2023)。第四,西方的经济权重也大幅下降,非西方世界开始探索货币替代体系。目前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的47%,而2001年为73%,这一趋势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五,过去被认为是公正标杆的西方新闻和新闻服务也面临信任危机,进一步削弱了西方的文化影响力(Nair,2023)。
33.昔日霸主罗马帝国的历史对于理解这些过程具有启发性。参照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六卷作品《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9),将西方当前的困境与罗马的衰微进行比较虽有些超前,但绝非无稽之谈。希瑟(Heather)和拉普利(Rapley)的文章符合这一思路,其认为罗马帝国在5世纪初处于权力鼎盛时期,在当时被西方人视为所知世界中毋庸置疑的霸权,但不到一个世纪这个庞大的帝国就走向崩溃。西方当前状况与之如出一辙:它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全方位对手;在冷战之后,世界的特点是西方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在经济表现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已浪费殆尽,同时还身陷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与其作斗争。希瑟和拉普利再次与罗马帝国进行了比较,强调罗马霸权的终结基本上归咎于罗马帝国本身,原因有二:第一,一直到5世纪的黄金时代,罗马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社会只存在些许不平等。第二,它成功地通过谈判和协议,让帝国以外的世界维持现状。通过这种方式,它享有系统安全、经济优势,此外,它还享有现代世界的典型优势,即跨越其领土边界的影响力和文化霸权。直到最近,西方国家还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它在华盛顿共识体系内巧妙进行谈判的同时,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并使西方全球化模式得到广泛接受。然而,由于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平等再次扩大,技术优势丧失,西方国家不再投入精力确保非西方世界参与华盛顿共识(如世贸组织改革已被推迟数十年),因此西方开始选择切断连接。为了改变现状,希瑟和拉普利首先提出建议,西方应放弃切断连接,避免走向集团化。此外,它应该采取一些本质上是左翼的政策来维持社会平衡,最为关键的是增加和扩大全球最低税。诚然,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实现全球最低税全球化,但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点,解决剩余的竞争力问题又无从谈起(Heather-Rapley,2023)。
34.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2022年春季致公司股东的一封信中写道:“乌克兰危机宣告着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的全球化的终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项目辛迪加》上发表文章,宣告世界秩序结束,其标题非常简单:“自由世界秩序,永垂不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习近平,2023)。至此,波洛的论述已完结。如果所有重要的参与者和大多数分析家都在宣布当前世界秩序的终结,那么它几乎不可能维持下去。(Forbes,2022;Reveel,2018;Ray,2022; Haass,2018; Sauer-Hawkins,2023。)
35.Brzezinski,2012.
36.虽然这份清单由我自己整理,但并非没有先例。约翰·伊肯伯里曾在其探讨民主未来的著作中提及了不少事件。这本书出版于2020年,因此伊肯伯里未能含纳随后的某些新事件。此外,我们还补充了几个早期事件。这些补充遵循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的“黑天鹅”理论,因此我们正在寻找可能对国际进程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外、不可预测的事件,或者可能产生意外影响的事件(Ikenberry,2020;Taleb,2010)。
37.福鲁哈尔(Foroohar)用新术语“后新自由主义”来描述新自由主义经济组织原则和模型的枯竭,并描述正在出现的新范式(Foroohar,2022)。
38.默里(Murray)认为,欧洲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渗透整个西方政治环境的问题,就是自尊的丧失。在西欧,大规模移民在精英阶层中获得强烈广泛支持,因为精英阶层不重视欧洲文化(Murray,2017)。而这种自尊的丧失,无疑使它们难以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里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39.德国教授、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安德烈亚斯·罗德尔(Andreas Rödder,2019)认为,欧洲最大的错误在于它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自己的战略。在较好的时期,欧洲有像默克尔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和危机处理高手,却从未制定出一个能够确保欧洲长期自主权的战略。
40.诸多著作指出,2020年是迄今为止全球化发生最大变革的起点。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不仅限于地缘政治变化,还包括经济变化(Ágh,2023)。一些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公众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到达顶峰(Menon,2022),还有些专家则认为是非西方世界反对美国主观解释规范(Walt,2023)。
41.在下文中,我们将主要讨论国际秩序受到侵蚀的问题。有人认为,我们也应关注世界秩序中参与者的变化,以及全球权力中心格局的演变。但我们此处采取了不同的概念路径,专注于动态流程而非静态方法。过程逻辑如下:随着单个行为体对秩序规则越发不尊重,新的权力中心应运而生,同时新的权力中心开始建立新的替代机构,这些机构正作为新的行为体登上国际舞台。而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这些新的行为体与权力中心,如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的崛起和非西方机构合作的新领域,这些现象被普遍视作规避既有规则的一种结果。
42.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却并不接受新自由主义原则,这并非中国经济模式所独有。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经济融合模式也是基于极为类似的方法(Gewirtz,2017;Di Maio,2015;Santiago,2015;Cui-Jiao-Jiao,2016)。
43.有关邓小平同志经济政策的更多信息,即出口、外国投资和技术进口驱动的扩张型经济模式(De Lisle-Goldstein,2019)。
4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中国,而现今这一代表权已被转移。
45.有关构成中美关系的复杂战略目标体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基辛格的著作(Kissinger,2011)。
46.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以上,而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长率不到4%(世界银行,2022)。当然,经济实力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影响力,但前者对后者的推动作用巨大。在这样的格局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至2023年中国占世界GDP的19%,美国占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b)。
47.《时代》杂志前外交政策编辑约书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一项研究提出后,“北京共识”一词进入西方政治词典。拉莫这一贴切说法表明,中国一直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模式融入全球化世界,但从未打算遵守“华盛顿共识”,尽管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做到这一点。(Ramo,2004)。
48.据中国政府估计,政府每年以直接补贴、税收减免、以远低于国际标准的利率发放贷款以及补贴出售建设用地等形式,向中国国内企业提供近2500亿美元的国家补贴。值得一提的是,这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1.7%,而美国的年增长率仅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4%,韩国仅为0.67%(Di Pippo-Mazzocco-Kennedy,2022)。
49.García-Herrero-Ng,2021.
50.Turner,2017.
5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于西方竞争模式的“重新诠释”并不代表着中国试图获取不正当优势。首先,中国文化并不是特别以竞争为导向,而这种独特性,也可能有助于中国在公共外交以及国际形象塑造方面获得优势。早在2008年,马克·雷奥纳德(Mark Leonard)就指出,中国正寻求在其政策制定中制衡美国的价值观:和谐合作而非激烈竞争,推崇和平而非战争,倡导多样性而非推动统一的西方价值观。建立“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Leonard,2008)。
52.Low-Salazar,2011.
53.SIPRI,2023.
54.Janardhan,2020.
55.IMF,2023.
56.Datt-Mahajan,2009.
57.Adhia,2015.
58.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没有任何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决议,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仍辩解称,他们的介入是为了避免种族灭绝,将此举定义为人道主义干预(Latawski-Smith,2003)。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也沿用了同样的逻辑。同样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任何决议授权的情况下,美国领导的联盟再次为其军事干预进行合法性辩护,称伊拉克未遵守安全理事会第1441号决议,不允许联合国观察员检查其潜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也引起了质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号决议规定,应建立禁飞区,并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平民。然而,一些权威专家(Haass,2011)表示,此干预超出了最初授权范围。2011年后,美国插手叙利亚内战,2015年后,法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插手。这些行动的法律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第2249号决议,该决议敦促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安理会没有授权单独的军事干预决议。
59.自2019年12月以来,美国一直插手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导致该机构陷入停滞状态。特朗普政府以需要进行全面的世贸组织改革为由,阻挠法官的任命。随后拜登政府也一直坚持这一立场,2023年2月,比利时表态,明确支持美国的立场(WTO,2023a)。而在2022年12月,百余位世贸组织成员呼吁美国停止阻挠法官任命的行为。
60.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审查在联合国大会中与美国保持一致投票国家的比例。最新的此类报告表明,在过去三十年中,没有一年有超过半数的国家与美国在投票上保持一致(DOS,2022)。近年来的统计分析(Ferdinand,2014; Binder-Payton,2022)表明,金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凝聚力日益增强,且它们越发倾向于与G7国家立场相反。
61.大多数干预措施注定要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国家不会在预算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而能够维持较低干预成本的国家通常又不具备民主化的适当条件(Downes-Monten,2013)。因此,此类军事干预措施通常不是很成功。安德鲁·J.恩特莱因(Andrew J.Enterline)的广泛研究表明,1800年至1994年期间,63%的干预措施未能实现其目标(Enterline-Greig,2008)。
62.Mearsheimer,2022。另见Desch,2007;Hend-rickson,2018;Risen,2006;Risen,2014;Priest-Arkin,2011;Savage,2017。
63.十多年前,布热津斯基勾勒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场景:美国将因自身的内部问题而失去霸权地位。然而,他也指出华盛顿共识体系不会被新的世界秩序所取代,相反,我们必须准备好面临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成为霸主,他们既不具备实力,也不具备国际合法性。因此,国际秩序混乱将以大国之间的持续对抗为特征。当然,布热津斯基受美国财政部乐观主义熏陶,只视此场景为最糟情况。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专家指出,美国最好不仅要关注其他强国,还要努力与中等强国和地区强国建立密切关系(Blanchette-Johnstone,2023)。
64.在《匈牙利战略之道》第二章第三节中,我们详细描述了自由主义的内部矛盾,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仅简要提及这些结论,并部分地加以引用。
65.霍姆斯·克拉斯特(Holmes-Krastev)表示,在中东欧地区的东欧集团崩溃后的三十年里,自由主义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的原因似乎显而易见。首先,在民主过渡期间,人们期望该地区国家照搬西方民主体制,却基本忽略了其自身独特民族特征。因此,西方基本上没有为中欧和东欧民主的发展留下空间。其次,西方的经济组织原则(新自由主义)失败了,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按照预期提高该地区生活水平。再次,虽然理论上他们是西方制度秩序的正式成员,但实际上,西方将中欧和东欧国家人民视为二等公民。最后,自由主义与该地区国家的社会自我形象并不匹配,因为该地区大多数人反对个人主义,奉行更加社群主义的原则(Holmes-Krastev,2019)。
66.西方世界对自身价值信心不足,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柏拉图的《智者篇》中就初现端倪,柏拉图认为,从原子论(物质主义、物理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美德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我们目前的议题而言,柏拉图的思想中值得借鉴的一个原则是,即使在古代,纯粹的唯物主义方法也显然必然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黑格尔(G.W.F.Hegel)对其中原因进行了最彻底的论证,他指出,当物理学家涉足价值领域时,他们往往无法看到价值全貌,过于抽象地对待价值,并在此过程中绝对化特定方面,从而在价值的基础上制造出了内部矛盾(Hegel,1979b)。那些谈论西方价值观侵蚀的人都以不同形式引用了这一论点。然而,福山并不是从此处采纳这条特殊思想史线索的,而是十分明了地从尼采那里接过,正如他的著作标题表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该标题极具说服力,因为“历史的终结”一词指出了福山思想中的黑格尔元素,而“最后之人”指的是尼采,后者经常站在黑格尔的对立面,因此我们注意到此处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综合体。尽管如此,这种“综合体”并非不合理。尼采在他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使用了“最后之人”一词,指的是一个虚无主义的个体,他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来到了历史的尽头(尼采,2006)。有趣的是,这个主题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Die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中也有所探讨。在这方面,需要明白的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有一些意识内容体现在历史发展中,其中包括“最后之人”的主题,这主要体现在古希腊的喜剧作品中。黑格尔写道,希腊喜剧的主角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独自留在舞台上,被众神抛弃(从而成为物理主义者),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众神皆已死亡。在他看来,这表明希腊文化已经达到顶峰,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变得空虚。“最后之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众神的抛弃,这在尼采那里也能找到呼应,他的著名论断“上帝已死,是我们杀了他”,摘自他的著作《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974)(原著: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与普遍看法相反,尼采并没有将这句话作为幸灾乐祸或是庆祝,而是作为一种警告:西方文明的物理主义和科学倾向终将导致虚无主义。福山选择尼采作为主题是否是因为他对物理主义的批判。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把这些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放在一起,他们的结论基本上指向同一个方向:当一个文明达到顶峰时,它通常不是被外部敌人推翻,而是被内部的不确定性推翻。我们还了解到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质,即它与唯物主义(或如今流行的物理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出现,因为物理主义的世界观破坏了文明赖以建立的价值观。虽然福山没有探讨物理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的联系,但他在作品结尾对这种虚无提出了警告(Fukuyama,1992)。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中概述了该过程的一种展开方式:为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发起的战争中,结果却导致这些价值观在推广它们的国家中被部分践踏。因为为了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政府甚至会使用与自由主义原则相悖的方法(Mearsheimer,2022)。我们要补充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违反规则不仅是对这些价值产生了负面冲击,违反规则的方式更是指明了自由主义价值根基不稳,因为自由主义内部矛盾存在导致了其更为强力的执行,反而导致了自我毁灭。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将普遍性绝对化,支撑特殊性的价值观就会岌岌可危。这并非仅是过去哲学家夸大的危言耸听;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观察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那些不信奉物理主义原则的人如今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Nagel,2012),另一位当代哲学家沙伦·斯切特(Sharon Street),在达尔文进化论(一种物理主义理论)如何削弱所有的价值现实主义中也呈现了这一点(Street,2006)。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斯切特对进化论的批评,而是反对价值现实主义的论点。
67.此外,博肯福德(Böckenförde)表示,现代国家的运作不仅仅是传统的,而且受到宗教价值观滋养(Böckenförde,1976)。
68.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种所谓“宪政爱国主义”的解决方案。其本质是对国家机构的忠诚,以及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上对法治机构的忠诚,可以取代宗教和民族价值观。以色列哲学家约拉姆·哈桑尼(Yoram Hazony)指出,这种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主张,此外,这种机械式形成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往往无法创建一个正常运作的社区(Honneth-Joas,1991;Hazony,2018)。
69.没有广泛的中产阶级,就无法建立运作良好的国家和民主,这句公理并非首次提到,甚至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这个阶层的公民在各国具备最大的安全性;因为他们自己不像穷人那样觊觎别人的财富,其他阶级也不像穷人贪图富人的财富那样贪图中产阶级的财富;因为他们既不遭人谋划,也不谋划别人,他们的生活没有危险。正因为如此,福西尼德(Phocylides)虔诚地祈祷:“在许多事情上,中间是最好的,愿我有一个中间的位置。”
70.金融策略师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认为,如果社会不平等不阻碍增长,国家经济就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由于不平等现象,国家倾向于引入广泛的再分配机制和援助体系,但这并不能刺激增长,反而会使公共财政失去平衡。国家也将因此无法应对哪怕最小的国际金融起伏,并甚至导致国家经济陷入长期衰退(Sharma,2017)。
71.“仁慈霸权”一词由罗伯特·卡根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该术语表明,美国在世界政治上的主导作用对整个世界是有益且积极的(Kagan,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