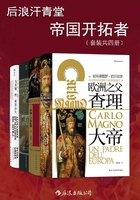
传统观念与政治宣传
特洛伊起源说
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查理出生以前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是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构建的。而当时宫相的儿子受教的历史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当时的人们用另一种世界观来解释法兰克人的历史。这种世界观在今人看来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对他们而言是确凿可信、毋庸置疑的。查理的同代人对自己本民族历史的了解还不如我们现在的史学家,他们确信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这一传说最早于660年左右记载在《弗雷德加编年史》(Die Fredegar Chroniken)中,差不多是查理出生前一个世纪。8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在蛮族战士与罗马世界接触以后,这种传说在他们之中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这似乎并不是学者的创造,而是一种流传甚广的传统观念。
特洛伊起源说明确表明了一种与罗马人有关的比较性甚至竞争性的意义。根据维吉尔的诗歌,罗马人从普里阿摩斯(Priamus)的儿子——流亡拉丁姆的埃涅阿斯这里继承了特洛伊的血脉。法兰克人则相信他们承自另一位特洛伊王子——法兰西欧(Francio),法兰西欧不仅把自己的名字赋予了他们部族,而且带领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西欧,定居于莱茵河畔。因此他们是罗马人的血亲;当埃涅阿斯的子孙(罗马人)逐渐衰弱,不再享有统领的资格时,这种亲缘关系使他们有权统治高卢乃至更广阔的地域。较之世俗之人,这个观念应该在教士中传播得更为广泛。但毫无疑问,从查理年幼之时,这个观念就逐渐灌输入他的思想之中,影响着这个后来头戴罗马皇冠的孩子。
有趣的是,法兰克人与罗马人是同宗血亲的观念并不尽是虚妄之词。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发现罗马帝国时期这两个民族之间是高度融合的,而这段历史在查理的时代已被人遗忘。法兰克人并不是野蛮地打过莱茵河边界,全部族大规模迁入高卢。在3世纪至4世纪,法兰克战士们为罗马服役,和平定居在帝国境内。事实上,法兰克人在罗马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完成了本民族的自我认同。3世纪时阵亡在东部潘诺尼亚行省的军团战士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墓志铭:“Francus ego cives, romanus miles in armis.”可以翻译为:“我属于法兰克民族,但拿起武器时,我是一名罗马士兵。”9这位战士很可能并不知道特洛伊起源的传说,但他对这一观念并不会感到惊奇。
上帝选民说
法兰克人的历史包含另一层意味,旨在强化自己是罗马继承者的主张。这成为他们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独特联系。这种联合可以追溯到克洛维皈依的时代,他在圣诞节于高卢受洗。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年份,但应该是496年。另一些日耳曼部族是受由希腊教会影响的传教士的教化而改宗基督教,他们信仰的是阿里乌派(ariana)。当时阿里乌派在东罗马帝国广泛传播,但在西部帝国鲜有人知。与天主教不同,阿里乌派信仰的基督,人性多于神性,其在本质上比圣父要低一些。阿里乌派回避了三位一体的复杂教义,这样的解释对于缺乏神学与哲学修养的部族来说,更容易接受。其结果是,在皈依阿里乌派后,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难以理解罗马天主教。他们不仅在教义上有分裂,在教会等级上也有竞争和分裂。在罗马天主教世界看来,这些蛮族是基督徒中的异端,他们比异教徒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
法兰克人到达高卢时,还是多神信仰,他们是在当地教士的监管下皈依的。因此他们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天主教的忏悔仪式。这种历史机缘对法兰克王国的未来产生了有利的影响:罗马-高卢的主教和元老贵族们发现和法兰克诸王合作更为便利,故把他们视为保护者而不是压迫者。因此,起码较于其他罗马-蛮族国家而言,这些国王能建立起相当有效的行政和财政体系。在罗马人眼中,他们是合法的政权。他们不是篡位者,而是如君士坦丁大帝时期以来一直统治他们的罗马皇帝一样,是上承神恩的统治者。
最重要的是,法兰克人信仰天主教,这使得他们能和天主教会的最高精神领袖——教宗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些圣彼得的继任者从理论上说依然继续臣服于远在拜占庭的罗马皇帝,人们依然认为他们要依靠皇帝来抵御外敌——比如信仰阿里乌派的野蛮伦巴第人,他们自568年进入意大利以来,就对罗马城构成了真正威胁。然而,拜占庭皇帝离这里太远,并且他们用希腊语祈祷,他们的宗教仪式在经历几代人的分隔之后也和拉丁教会日渐不同。
在这种种原因之下,教宗意识到寻找一个在地理和信仰上都更为接近的保护者的意义。他们唯一的候选人就是法兰克国王。于是教廷开始宣称法兰克人是上帝新的选民。教宗司提反二世756年给丕平的信中就写道,是圣彼得本人亲自向法兰克人布道,告诉他们,上帝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民族,注定要承担和罗马人一样的伟大使命。10几年之后,新任教宗保罗一世打破古老的传统,没有将教宗选举的结果照会东罗马皇帝,而是告知了丕平。他对法兰克人说:“你们民族的声望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法兰克王国在上帝面前光彩夺目。”他接着引用《新约》:“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9)11
这封信并没有被置若罔闻:法兰克人最重要的法律文献——国王丕平于763—764年(查理时年21岁)下命起草的萨利克法(lex Salica)——的开篇就写道:“自未开化之时起即上承天命、声名卓著、战时骁勇、和时忠贞、皈依天主、不信异端的法兰克人。”法兰克人认为自己不仅和罗马人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了他们。毕竟他们以武力击败了尼禄与戴克里先的继承者,这两位罗马皇帝都曾迫害过真正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以武力推翻罗马压迫的民族,他们接受了洗礼,并把那些被罗马人处以火刑、斩首、兽决的圣徒之遗骸,镶以黄金和珠宝。”12
孩提时的查理,是在自己父亲的宫廷里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不会像现代史学家声称的那样,认为法兰克人是一个没有原始内聚力的部落联盟,是在那些为罗马服役的军事领袖的不断进取之下,逐渐转变为一个国家的。对他而言,法兰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和罗马人一样高贵。并且和他们一样,法兰克人注定有朝一日要统治世界,维护基督教信仰。他们的一切事业都是在神意的指导和庇佑之下,因为他们是基督之民,就和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是上帝的选民:“荣耀归于基督,恩泽法兰克人。”萨利克法的前言如是写道。这个“新以色列”的君主不仅像查理·马特那样,是一位新的约书亚,更是一位新的摩西、新的大卫、新的所罗门。这种观念不仅流传在高卢主教们的逢迎讨好之辞中,也反映在罗马教宗的官方公告中。如果我们以查理从父亲手中继承法兰克人的领导权之时为始,去理解查理的整个生涯,我们就要记住,这种观念不只是舆论和看法,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家族传统
对丕平的儿子而言,本家族的历史也远不是我们之前篇章中所说的那种枯燥的统治者年谱。查理宫廷中的一位伦巴第学者助祭保罗(Paulus diaconus),应查理之命记述了一位本朝创始者——梅斯主教圣阿努尔夫的故事。他依照皇帝的要求写道,一次阿努尔夫请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他将一枚戒指扔进摩泽尔河作为忏悔的信物,发誓直到戒指回到自己手中,他才能得到宽恕。多年之后,一名厨师为阿努尔夫主教烹鱼时,在鱼腹中发现了这枚戒指,于是上帝宽恕了阿努尔夫的罪过,并归还了他的信物。
这个戒指扔入水中又在鱼腹重现的故事,显然是许多神话故事中都出现过的民间文学母题。有些人认为这类虚构故事有着极其悠久的起源,在发现查理将这类神话传说运用到自己家人的真实故事中时,他们都会觉得这很迷人。然而我们都不该忽略这个故事的意识形态暗示。这个故事极有可能就是在宫相的宅邸里口述,然后写下的,所以查理一定在童年时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奇迹中所赞扬的阿努尔夫的圣洁之名,必定要在他的后世子孙中代代传扬,让他们相信自己属于神赐天恩的家族。助祭保罗将这个故事写进自己的著作《梅斯历代主教纪》(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也就顺理成章了。并且他还写道,阿努尔夫的福报使他的后裔有权统治法兰克人。13总而言之,这一作品是受查理出于政治目的委托而写成的。
自查理儿时起,官方的宣传就已经在强化这么一种说法,那就是丕平家族奉天承运,注定要统治法兰克人。丕平的叔父奇尔德布兰(Childebrand)以及后来他的儿子尼伯龙(Nibelung)都继续编写《弗雷德加编年史》,他们在文字中都暗示,查理·马特和他儿子取得的胜利都符合神意。14换句话说,就是神选王朝将统领神选之民。这个戒指的故事,查理七八岁时听到,并没齿不忘。他此时听到也是恰如其时,此时他的父亲丕平不再满足于以宫相的身份统治法兰克人,决定称王的时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