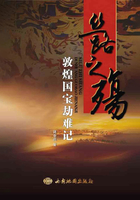
第二章
秘窟沉睡历千载 天响惊雷宝洞开
韩禄进城,挂着一褡裢木杵、面杖、磬棰在街巷集市上转悠叫卖,一连几天也卖了些小钱。没想到冤家路窄,一天下午竟又与县衙的差役何林狭路相逢。那恶棍酒后撒泼,仗势欺人,先是强行勒索,继又寻衅滋事。韩禄正被纠缠得无法脱身,幸有二先生张鉴铭不期而至,掏了点钱打发何林,这才替他解了围。二先生早已从朱掌柜处得知莫高窟引水冲沙取得成效,原以为韩禄已离开那里,听他解释后又关切地问:“家里有困难,怎么不告诉我们?”
韩禄腼腆地回答:“一再打扰,实在不好意思。”
张鉴铭直言相劝:“那有什么,都是乡里乡亲的,亲帮亲,邻帮邻,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你协助王阿菩维护莫高窟,不也是在为乡里尽力么!走,现在就去我家!”他不由分说,叫上韩禄便走。
张举人家又接济了韩禄一些粮食,当他牵着驮粮的马匹走出张家堡与主人道别时,二先生又对他殷殷嘱咐:“把粮食送回家后,尽快回莫高窟去。近日多次听说南山很不安宁,王阿菩体弱,三青年幼,我们很担心土匪去骚扰佛窟!”
本来韩禄心里就不踏实,听二先生叮嘱后心里更是牵挂,他往家里送了粮食,也顾不上与儿女们亲热便急匆匆赶回莫高窟。当他骑马走近下寺,见寺门损坏,门前地上散落着器物及粮食,深感情况不妙。他立即跳下马背,跑进寺院,不停地呼唤:“王师父!”“三青!”惊慌失措地在各房间进进出出,但除了到处都留下土匪乱翻乱砸的劫后遗迹外,整个寺内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心乱如麻的韩禄,沿着崖壁由北向南把下层的洞窟细细搜索了一遍,除了安坐莲台和静立法坛的菩萨之外,根本不见师徒二人的身影。
心急如焚的韩禄,费力地爬上洞窟高处,放声向四野呼喊,直喊得声嘶力竭,也听不到一声回应。
焦虑万状的韩禄寻罢洞窟又寻至中寺,一进寺门便见寺院住持红衣大喇嘛被捆绑在木椅之上。他连忙替大喇嘛松绑,在询问情况后,又急切地返回下寺。但就在他快步行进中,发现距离寺院不远的草地上留有明显的血迹,循迹望去,突然看见附近草丛中躺有一人。他急出了一身冷汗,生恐那是王师父或三青,惊恐不安地走近细查,才看清是被土匪杀害的一具香客的尸体。这令人发指的暴行,不仅令他深恶痛绝,而且更增添了他对王道长和三青的担心。
心力交瘁的韩禄拖着疲乏、困倦、饥饿的身子回到下寺,走进伙房想看看有没有充饥的东西。但四下一看,别说吃的,连平日盛茶的瓦罐都给打碎了,气得他一屁股坐在一只翻扣在地上的大柳筐上,十分纳闷地暗自寻思。突然,他觉得柳筐里有什么响动,吓得他急忙起身把柳筐翻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三青被土匪结结实实地捆成一团硬塞在柳筐里,韩禄掏出他满嘴塞的棉絮,一面为他解绳一面急切问:“王师父哩?”
三青吐出嘴里乱塞的东西,语无伦次地回答:“师父,师父,你没见到?”
“我进城了!王师父哩,遭土匪绑走了吗?”韩禄提心吊胆地追问。
“你说师父遭土匪绑走了?”惊吓之余的三青似有几分糊涂。
韩禄拍拍三青的脑袋:“三青,三青,是我在问你,王师父哩?”
“呸,呸!”三青直盯着韩禄,眼睛眨巴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说,“师父,师父前两天进城借经书去了。”
听过三青的回答,悬在韩禄心上的石头这才落了下来。
过了几天,王道士回来了。他喜滋滋地从褡裢里取出《道德经》《玉皇经》《三宫经》《清静经》等厚厚一叠道经得意地说:“看,在西云观借的,真给面子,借给这么多。不过他们也要用,得尽快送回去。”
三青好奇地接过经书在手里掂掂,又看看封面上那些他根本不认识的字,多少有些惊讶地问:“哇!这么沉,这么多,师父,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我小时候家里穷,肚子里喝的墨水不多,怎能有那样的本事。”王道士对徒弟实打实地说。
三青又问他尊敬的韩大哥:“你怎么样?韩大哥。”
韩禄更是老实巴交地回答:“我大字识不了一箩筐,别说看书,听见说书都心烦。”
三青捧着书傻眼了:“那怎么办?人家不是说要尽快送回去吗?”
王道士好像故意卖关子,见三青急成那样,脸上露出几分憨笑,从容地宣布:“莫急、莫急,张举人家二先生比你想得周到,他给请了个姓杨的先生来替我们抄写一份,这不,我把笔墨纸砚都背回来了。”他随手把沉沉的褡裢递给韩禄。
三青听后多少有些担心:“人家先生来了,咱们这儿又没个书房,在哪儿摆书桌呀?”
王道士早有打算:“我们这儿虽然没安闲的书房,可有的是清静的佛窟。”
“你看,人家张家堡子的书房多美气!”三青仍在犟嘴。
王道士哈哈一笑:“你再想想,我们这儿的佛窟多神气!”
其实三青也是嘴上说说而已。师徒简单商量后,王道士便拿定主意安排打扫16 窟。他之所以选了这里,一是它的洞门外有一座依山而立的三层楼阁七佛殿,虽年久失修已破败,但从外观看,在莫高窟众多的佛窟中,它也是鹤立鸡群,算得上仅次于大雄宝殿(五层楼)的第二高层建筑;二是它正好在下寺以西不远处,近近的距离便于进出、关照;三是它曾长期被干燥的流沙封埋,窟内极少损坏,环境较好;四是它位于下层洞窟北端,从此下手逐次向南清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随着王道士、韩禄、三青的清扫,曾被黄沙长期掩埋的 16 窟渐渐展露出它那高大、幽深的容貌。在微弱昏暗的光照下,一尊尊佛像影影绰绰,一幅幅壁画朦朦胧胧。这座初露尊容的古窟,既显示出庄严、肃穆的神威,又笼罩着神奇、神秘的色彩,确实令人敬畏。特别是当洞门大开,流沙逐渐除去后,阴森森的窟室深处一股股凉气外溢,实沉沉的洞门上方一阵阵热风内渗,一冷一热在甬道中交汇,幽深的洞窟里除了飕飕风声和王道士掀沙的响声外,沉静得令人恐惧,令人发憷。
清扫洞窟的工作进行得顺顺利利,王道士一锨锨往柳筐里装沙,韩禄、三青一筐筐往洞外抬沙。当除去黄沙,一侧洞壁壁画供养人中露出了一位身着红衣的女子。王道士见后闪念之间想入非非,禁不住有些走神,刚刚联想起芙蓉姑娘留给他的红绸巾时,突然听见“轰隆隆”一声震响,像洞窟的穹顶响彻一声霹雷,像山崩地裂掀起一阵震颤,震得王道士昏头昏脑地扔下木锨,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以为又是自己动了杂念,闯了大祸,引得天神震怒。
三青、韩禄抬着柳筐进来,见王道士瘫倒在地,不知他是受了伤还是得了病,急忙围了上去,一边扶他一边问:“师父你怎么了?”“王师父,出啥事了?”
王道士惊魂未定,呆若木鸡。他双目凝望着窟顶,嘴唇不住地嚅动,但又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韩禄和三青连忙把他扶出洞外,陪他休息了好一会儿。清醒过来后,王道士又疑神疑鬼地返回洞内查看,见佛窟未塌、佛像仍在,心里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总害怕又有什么大祸降临。
深夜,下寺屋内,一支残烛的荧荧烛光忽忽悠悠。土炕上,韩禄、三青已经入睡,而王道士却紧盘双腿,微闭双眼,两手捧着一本借来的道经,一动不动地坐在炕头苦思冥想。躺在王道士身边的三青翻了个身,睁开眼睛见师父捧着经书在打坐,不禁问:“师父,你还在诵经?”
王道士好像还笼罩在洞窟震响的恐惧之中,他似觉三青在说话但又没听清说的什么,反而问道:“三青,你们在洞外没听见响雷?”
“没有,大晴天的,根本没有打雷。”
王道士迷迷糊糊的:“真没有响雷,你不会骗我吧?”
“谁敢骗你,不信你问韩大哥。”
“这就怪了,我明明听见洞顶响了炸雷,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王道士沉浸在幻想之中……
忽忽悠悠的烛光熄灭了,落入沉沉黑夜包围的王道士,渐渐地进入了梦境。他看见蓝蓝的天空好像一幅高挂穹顶亮丽无比的天幕,白白的浮云恰似一团团随风起舞千变万化的飞絮,而他正依托着一团白云,飘飘浮浮乘风直上蓝天。在他眼前:天女散花,乐伎飞舞,仙乐声声,霞光四起……
面目慈祥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脚踏莲花、手托宝瓶徐徐飘来,摇动手里的柳枝轻洒净水,似要渡他出苦海……
神采飘逸的张天师,脚踩祥云缓缓而过,挥动手中的拂尘,像要掸去他的俗念……
灿烂霞光中,释迦牟尼现身了。高立于佛坛之上的佛祖对着他正言教化:“尔须了断情欲尽心守护佛窟,才能修成正果。”
七彩祥云里,太上老君显形了。端坐于青牛之背的道君指着他朗声训示:“汝要努力弘扬道义,方得羽化升天!”
看着天宫中的千变万化,望着若隐若现的诸佛诸神,听着佛祖、道君的谆谆教化,王道士若痴若迷,似梦似醒地频频下拜,连连称诺:“弟子谨遵师命!”“弟子牢记不忘!”……稍后,风起云乱,王道士眼前的天宫消失了,盘膝打坐的他又回到沉沉夜色中,似幻似真地对他梦中的天宫念念不忘,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弟子谨遵师命!”“弟子牢记不忘!”
王道士的呓语声惊醒了三青和韩禄,三青急忙呼唤:“师父!你怎么了?”
呼唤声中,王道士大梦方醒。他睁开眼直直身,先是把梦见佛祖、道君显灵的景象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通,等他们相继入睡后,心里很不踏实的他又轻声溜下炕去,找出一块黄绫绸,神经质地把那片绣有“义”字的红绸巾包裹起来藏进了一只小木匣里。
又经几日扫除,终将 16 窟打扫干净。按王道士安排,在离洞口不远处的甬道北墙下新摆设了一张条桌、一把木椅,桌上陈设了笔墨纸砚,煞费心思地为要来抄写经书的杨先生精心地布置了一间特别的“书房”。
杨先生来了,这是一位中等身材、身体瘦弱、面容清癯、书生气十足的先生。他衣衫虽旧,但洗得干干净净;年岁不高,但蓄的胡须很长。他走路慢条斯理,讲话轻声细气,但不时又露出生不逢时、怨天尤人的感叹,处处都显示出顾影自怜、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读书人气质。原来他确实是一介书生,早年也曾在肃州、凉州、安西官府干过差事,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丢了饭碗。安西家中虽有些薄地尚可维持生计,但他既不懂农事,又无缚鸡之力;既放不下身份,更拉不下面子。只得远离家小,落魄在外,靠着笔下的一手好字,替人抄抄写写,聊以为生。此次受张举人家之请来莫高窟为王道士抄经,也是想离开喧闹纷争的城市,给自己找个清闲与安静之地。
杨先生是第一次来莫高窟。当王道士陪他进入 16 窟后,高大深幽的窟室,彩色斑斓的壁画,慈祥端庄的佛像,令他惊奇不已。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走出窟室后,王道士竟指着甬道北墙下的条桌恭恭敬敬地对他说:“杨先生,这洞窟虽然简陋,却也清静凉爽,你的书桌就安排在这儿。”
杨先生既露出惊讶之色,又似有不满之意。他立在桌旁,看看桌上摆的文房四宝,客客气气地问:“就让我在这儿抄写?”
王道士敷衍道:“你也看到了,寺院太小,房舍破旧,真没个合适的地方,只得委屈你了。”
三青见杨先生不肯落座,主动帮师父劝解:“杨先生,这洞里冬暖夏凉,师父说菩萨和神仙还在这儿显过灵!”
韩禄也跟着帮衬:“杨先生常坐这儿抄写经书,积善积德,说不定哪一天功德圆满也会得道成仙哩!”
“啊,我只是靠抄抄写写挣几个小钱聊以糊口的凡夫俗子,哪敢有什么得道成仙的痴心妄想。”杨先生不便过多僵持,只好对王道士头点称谢,勉强坐下。
王道士毕恭毕敬地把几本道经端端正正地呈放在条桌正中,双手抱拳施礼:“杨先生,这就是我从西云观借来的经书。”
坐得端端正正的杨先生伸手取一本经书翻了翻,又取了纸张放在面前说:“那我就动笔了!”
韩禄见状,示意三青研墨……
杨先生提起毛笔润润墨正要下笔,王道士又想起了急事:“杨先生,这里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浴佛节快到了,你先给写几个字吧!”
原来敦煌这座四海闻名的古城,不仅以佛窟多、佛寺多、道观多称雄,而且以节日多、庙会多闻名。在俗称“四大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五月初五端阳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冬至节)“八小节”“二十四个末糊子节”之中,仅以元宵节而言,相传在汉唐时期,敦煌城元宵灯会的规模就列在京都长安之后,江苏扬州之前,在全国排名第二。

(莫高窟浴佛节会场)
在几乎月月有节日、天天有庙会的敦煌,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可以说是四方百姓最崇奉的节日之一。因为相传这一天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所以每逢节日庙会,各地的善男信女都要到莫高窟敬香、拜佛、还愿,乞求消灾免难,岁岁平安。王道士请杨先生写字,就是为节日佛会做准备。
经王道士等初步清扫过的莫高窟,又迎来了浴佛节庙会。自农历四月初一开始,各地的善男信女、香客游人,或携友相伴、举家同行;或徒步跋涉、骑马、骑驴、骑骆驼;或乘马车、骡车、大轱辘牛车,穿沙漠,越戈壁,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他们有的备足了馒头、烤饼、油糕等素食品,以供往返之用;有的带上米、面等主副食及铁锅等炊具,一路就地搭灶做饭,解决生活之需;路途上,一些积德行善的人,在道旁临时搭棚、砌灶,设立供行人歇脚饮水的“茶房子”;佛窟前,各寺的僧侣、道人也烧上茶水、备足柴火,敞开膳堂、伙房大门,任由香客、游人使用……盛大的佛节庙会,不仅是四乡信徒朝圣敬佛之日,而且是八方人士游春观光之期,真是盛极一方,热闹一时。
节日庙会期间,在绿树覆盖的林荫中,随处都有没挤进洞窟,没住上寺院的香客、游人。他们有的搭起帐篷落脚安身,有的铺上毛毡席地而坐……在清流潺潺的水溪边,有人烧水煮茶,有人支锅做饭,有人围坐而食,融融乐乐。有些人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在弯弯曲曲的小道旁,有售卖香烛的商贩,有烤烧饼、炸油糕、拉条子、煮粉条、卖酿皮凉粉的小摊……在芳草萋萋的草坪上,有人舞枪弄棒,尽力展示武艺;有人拨动三弦,吟唱敦煌曲子;有人合着铿锵的锣鼓唱秦腔;有人随着悦耳的琴声唱眉户;有人清唱民间小调……平时莫高窟前空旷宁静的大泉河畔,如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乐声不绝,笑声四起,成了欢腾的海洋。
按佛经所说,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出家、成道、涅槃均在四月初八。但中国佛教以四月初八为佛诞生日,二月初八为佛出家日,十二月初八为佛成道日,二月十五为佛涅槃日。又传说太子(释迦牟尼)诞生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故每逢四月初八,莫高窟都要在大雄宝殿为太子隆重举行“浴佛法会”。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八,高峻的大雄宝殿内,烛光闪烁,钟磬齐鸣。在旗幡舞动处、香烟缥缈中,气度宏伟,高达 34.5 米的弥勒佛金身巍然耸立。千秋岁月,大佛始终以他温厚慈祥的笑脸,面对纷争不息的大千世界;用他深邃睿智的目光,俯视着蜂拥而来的芸芸众生。大佛像前神桌上,玉雕太子像被供奉在一只盛满香汤的大盆里接受僧侣和信士的沐浴。红衣大喇嘛用藏语念诵经文,众多的善男信女拥来挤去。有的进香上烛,顶礼膜拜,以显示信仰的虔诚;有的敬奉瓜果,献上美食,以表达对佛祖的崇敬;有的还愿施舍,为儿孙、为来世积善积德;有的敬奉经幡锦幛,以了却此生此世许下的誓愿;更有些心灵至诚者,在手摇法铃、口中念念有词的红衣大喇嘛指引下,从佛座左边的观刹洞钻进,再从右边的洞口钻出来。以求消灾弭难,增福增寿。
当大雄宝殿法事兴盛、人声鼎沸之时,“三层楼”下杨先生抄经书的16 窟前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敞开的洞门两侧,贴上了杨先生书写的楹联:维护佛窟修正果;弘扬道义求升天。洞外左右设了两张条桌:一张上摆有茶壶、茶碗,三青侍立一侧供应茶水;另一张上摆有功德簿、功德箱,杨先生坐在桌后提笔登记施主们的布施。
许多从大雄宝殿出来手捧香烛,继续沿着各洞窟逐一上香的善男信女,经过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慢慢走向 16 窟时,无不由衷地发出赞扬之声:“下寺的道人还真勤快!”“搬走这几百年的沉沙也真不容易!”“看来这佛地仙境又兴旺了!”……
恭候在洞门前的王道士身着干净的道袍,精神焕发地接待走进来的各方香客、游人。他不停地与客人相互施礼、相互问候,融融洽洽,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
韩禄陪着张举人三兄弟和朱掌柜等走过来了,围在王道士身旁的人们客气地让开一面。性格豪放的武举人张壶铭一见王道士便抱拳施礼,赞不绝口:“王阿菩,辛苦一年多,清除了百年积沙,功德不小呀!”
王道士在赞扬声中显得有些拘谨,他十分谦恭地回礼相答:“这都是各位施主的功德。贫道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何足挂齿!”
张盘铭迎上问:“王阿菩,说一说下一步还有什么宏愿?”
当着众人面前,正是寻求施舍的好时机。王道士抓住机遇,毫不迟疑地指点前后左右,和盘托出了面临的诸多问题:“几百个佛窟要清扫,破损的门窗要修缮,‘古汉桥’、古栈道要修补,‘三层楼’也亟待重建……”
张鉴铭见他言犹未尽,追问道:“就这些?”
王道士稍稍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如蒙众施主成全,贫道还想把下寺改为道观,重建道宫,供奉道君。念诵道经,弘扬道义,引人向善。”
王道士之言一出,当即得到周围信奉道教人士的认同,张鉴铭也是喜形于色,大加赞许:“多年来,莫高窟上、中、下寺均由红衣喇嘛住持,他们做法事我们看不懂,他们诵番经我们听不懂,既难知其真谛,更难得其教益。王阿菩立愿建道观、诵道经,方便大众潜心从善,这不仅是宏图大业,而且是大善之举,相信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帮助!”
张鉴铭的话代表了许多信士的心意,所以他的话音方落,周围的人群中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得到众人支持的王道士更是欣喜不已,他向大家施礼致谢后,便引导张举人家三兄弟及朱掌柜等人入洞参观。进入洞门没几步,张鉴铭便问王道士:“你听见天雷震响的就是这个洞吗?”
“是这个洞。”王道士肯定地回答。
张壶铭有些不解:“这就怪了,怎么洞里响雷王阿菩能听见,韩禄、三青却听不见?”
王道士趁机吹嘘:“我看这是个神洞。各人的修炼不同、自然感悟不同。”
“如此说来,王阿菩不是神仙也是半仙了。”朱掌柜禁不住插了话。
听到这里,张盘铭打开了话匣子说:“很早以前就传闻莫高窟有个神洞叫‘黑风洞’,此洞可通东海会见老龙王,可通南海朝拜观世音。据说有一天,一只黄狗经过被黑风吸入洞中,守寺僧人怕凡人被吸走,用石板堵塞了洞口。那黄狗在洞中跑了三天,这才从敦煌城西150里的寿昌海钻了出来,与镇守鸣沙山的神龙相遇。后又有海马来到寿昌海与神龙争斗,相持不下,海马便隐藏于水中。聪明的神龙化为土人守候于海边,终将海马捕获敬献给汉武帝。武帝见此马体态魁伟,骨骼非凡,宣称是他最崇敬的太乙真人所赐,故命‘太乙天马’,并作‘太乙之歌’称‘太乙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聘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朱掌柜曾听人讲过,有一次县城城隍庙水井里掉下两只木桶,过了一个月一只从月牙泉飘出来,又过了几个月,另一只出现在寿昌海。
张鉴铭也听说过有人千方百计在莫高窟寻找“黑风洞”都没有结果。后有一位老和尚宣称,“黑风洞”是通海之洞、上天之洞,凡夫俗子是找不到的。只有等到佛祖显灵,晴天响惊雷,神洞才会打开再现于世。
众人的讲述,听得王道士多少有些心神不定。他陪同大家在窟里参观,一边又忍不住地想:“自己听过的响声会是晴天惊雷吗?”“这儿会是黑风洞吗?”“神洞真的能通海上天吗?”……正在胡思乱想的他,忽地被一声惊叫“快看!”镇住了。
原来是他们一行刚从光线昏暗的窟室出来,面对从洞外射入的强光,眼明口快的张壶铭意外地发现甬道北墙绘有壁画的墙面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急忙止步,招呼大家去看。
张鉴铭看着裂缝揣测道:“王阿菩,这是天响惊雷震裂的吧?”
王道士深感意外:“是吗?”
“看来这个洞真有些玄妙!”张鉴铭惊叹不已。
朱掌柜随声附和:“会不会就是‘黑风洞’?”
一阵议论让周围的香客、游人听见后,有关“黑风洞”的传言便像长上了翅膀,随风四散。有人说大晴天王道长听见了天响惊雷;有人说那就是四通八达的“黑风洞”;有人说通过“黑风洞”可以上天;有人说王道长就从洞里去西云观借过经书;还有人说那洞外的黄沙,都是引西王母瑶池的水来冲走的……各种传言愈传愈远,愈传愈奇,愈传愈玄。
众说纷纭激起了香客游人们的兴趣,许多人便争先恐后地向 16 窟拥去。
传闻的魅力实在难以估量。没过多久,对“黑风洞”再现信以为真,幻想升天的善男信女们便把 16 窟团团围住,挤得水泄不通。来得早的钻进洞去不愿出来,来得晚的跪在洞外燃烛焚香,顶礼膜拜。
浴佛节佛事过去了两三天,曾驻足于大泉河畔的香客、游人已渐次离去,而滞留在16窟内外的善男信女却有增无减。对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愈来愈担心的王道士,几次前去劝说。但由于他既说不清又道不明,听话的人又一个比一个更固执、更迷信,有的断章取义,有的各取所需,再加上各自的推想、臆测,使得王道士的解释,反而火上浇油,让人更感扑朔迷离。结果是杨先生不顺心,不能继续抄经;王道士不放心,不敢出去化缘;韩禄不安心,不便回家探亲;连三青也不称心,不便打扫洞窟。原来平平静静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不但让人有些无所适从,而且更不知会出现什么结局,造成什么后果。
如此局面又延续了两天,事态愈来愈严重。16 窟内外的香客不见减少。那些留在洞外的人有吃有喝,可以自由行动,并不怎么令人操心;而那些待在洞窟里的人,听说有的已经几天水米不沾,一心只想得道成仙。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弄不好便会闹出人命来。王道士心有隐忧,但又无计可施。好在杨先生是在衙门里见过世面的人,多少有些应急的经验,这才想出了对付的办法:
首先是杨先生去洞外的香客中走了一圈,说说理,吹吹风,试图再做一些劝说,却引得一些香客围着他争先恐后地诉说:“不是我们愿意待在这儿,是老人们在洞里不出来,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听说洞里有路通天,谁还肯出来呀!”“我们只好等着给他们送终了!”……
眼看杨先生劝说没有什么效果,只得由王道士出面。他挤进窟室,只见佛像前、佛坛下,像泥塑木雕,散坐着不少上了年岁的老人。这些人有的精神尚能支撑,盘着腿正襟危坐;有的饥渴难耐,已经东倒西歪;有的显然体力衰竭,已经困伏在地。面对如此情景,王道士竭力模仿静海法师和马道长劝人为善、悲天悯人的语调,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各位善人,玉皇大帝给每个人都定了天年。到了时辰,你不走也得走;不到时辰,你想走也走不了,这就是生死自有天定。至于升天入地,那得看你的德行,你的善举。为善积德之人,不论在哪里都能立地升天;邪恶无德之人,哪怕就在天门之旁也不能进入天堂。至于黑风洞,那只是一种传闻,连贫道也不知它在哪里。所以奉劝大家还是各自回家颐养天年,多多积德积善吧!”
部分静坐的老人听过王道士劝解后,好像有些回心转意,但看看左右的人均无动于衷,也不敢有所举动,窟室里依旧处于僵持的局面。
王道士规劝不成,万不得已,只好采取最后一步行动。他吩咐韩禄、三青按事先布置,立即动手向洞门边搬砖、运土、担水……守候在洞前的香客越看越是纳闷,终于有人忍不住地打听:“小师父,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韩禄故意大声回答:“昨天晚上有神仙给道长托梦,说佛窟本应是安宁清静之地,可近几日洞窟内不仅人声嘈杂,而且还有人拉屎拉尿,实在是对佛不敬之举,所以指派我们立即砌墙,把洞门堵塞起来!”
有人听后惊问:“那洞里的老人咋办?”
三青的声音更大:“师父说了,他们要是愿意,就留在洞里给菩萨做伴吧!”
眼看韩禄取砖,三青和泥,真的要动手封洞。突然有人高喊:“等一等!”
周围的人争先恐后冲进洞去。不一会儿工夫,有的拖,有的推,有的背,有的抬,终于把那些坚守在洞内的老人们一个个接出来了。
16 窟传闻惹出的风波平息后,韩禄抽空回了家,原来虚张声势的砌墙之事也告中止。杨先生又天天进洞去继续抄经,静寂无声的佛窟里没有外人干扰,自己家里也没有太多牵挂。他像远离喧嚣红尘的闲云野鹤,过得自由自在。
为了节省,洞窟里没有点灯。杨先生只得把条桌摆放在距洞口不远的甬道上,紧靠北墙,坐西向东,借着洞口射入的光线,慢条斯理地在白纸上留下一行行墨迹,写得累了便摘下老花眼镜,捧起他随身不离的白铜水烟袋“咕嘟嘟、咕嘟嘟”地抽上几口,偶尔还唱一段秦腔或哼几句乡曲俚调,显得十分安适、惬意。
杨先生点烟不用纸捻,而是就地取材,用荒漠戈壁生长的芨芨草秆,干巴巴的草秆又长又细又易着火,点着以后那小小的红红的火头缓缓慢慢地燃,那白白的轻烟晃晃悠悠地飘,望着望着很容易把人带入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遐想之中。
一天,当杨先生过足烟瘾,仰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时,他的耳边突然出现韩禄的声音:“杨先生常坐在这儿抄写经书,积善积德,说不定哪一天功德圆满也会得道成仙哩!”接着又传来二先生张鉴铭的声音:“‘黑风洞’是通海之洞,上天之洞,凡夫俗子是找不到的。”
正沉浸在快意中的杨先生,猛然察觉点烟的草秆已经快烧手了。他赶紧坐直身子,连忙又挑选了一根又直又长的草秆,点燃后顺手插入北墙的裂缝,奇怪的是那裂缝好像深不可测,以至草秆竟不见触底……他凝视着那彩绘佛画的墙壁暗自发愣,伸手去触摸裂缝,细微的裂缝冷冰冰,似有一股寒气向里抽吸。他缩回手来下意识地自问:“难道这是黑风洞?”就在他疑惧丛生、惊恐不定时,冷不防洞外又传来巨大的响声,吓得他魂不附体,抓起桌上的经书,跌跌撞撞地拔腿便跑,及至跑出洞门,被附近崖上塌落的土石残木挡住去路,这才发出一声惊叫:“塌洞了!塌洞了!”
王道士和三青闻声跑来,见杨先生脸色煞白、惊恐不安地瘫坐在远离洞门的地方,急忙上前搀扶。王道士问:“洞里塌了吗?”
“塌了吗?没看清楚……只是墙缝里抽风……凉飕飕的……也许是黑风洞真的在那儿!”惊魂未定的杨先生结结巴巴连想带猜地说了一通,并表示他坚决不再进那里去抄经书了。
王道士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既不便勉强杨先生再去 16 窟,也不敢让自告奋勇的三青进去,直等到韩禄探亲回来,才陪着他和三青壮着胆进去查看。但转了一圈,见洞内并没有坍塌的痕迹,只不过通道北墙的裂缝好像延伸得更长、开裂得更宽,他们感到有些奇怪,不由自主地围在那里,仔细地研究起来。
王道士让三青取来一把又细又长的线香,由他和韩禄从杨先生插过草秆的地方开始,沿着裂缝向上、向下把一根根线香小心翼翼地插进去。插一根又一根,除个别不慎折断外,几乎根根均未触底。而当一把线香插完后,那些露出的香头又正好排成一条直线,深感意外的韩禄抓起一根木棒,在裂缝两侧敲击,静寂的洞窟里立即回响起实沉沉和空洞洞两种迥然有别的声音。
三人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又相互对视了片刻,王道士手指墙壁右下角推测:“这一片是空心,墙里可能有门?”
“真要是门就把它打开!”韩禄扔下木棒抓起铁镐准备动手。
“不忙!”王道士横身护住墙壁,“佛窟里怎么能随便动土?”
显然支持韩禄的三青争辩道:“师父,那天张二先生说‘晴天响惊雷,神洞再现世’,你不是早就听见雷响了么?”
“那……那倒也是。可真要是打开了,就不怕我们像黄狗一样被黑风吸走?”
“那我们就去南海朝拜观音菩萨。”
“是呀!谁不想去朝拜,但就不知道洞中的佛祖,天上的道君让不让我们随便动土?”
“那你就赶快去问问呗!”
在三青的提示和催促下,他们随即在 16 窟前设起了供桌。王道士亲自点上一簇线香,燃起一对蜡烛,遥对三层楼,顶礼膜拜。韩禄和三青静静地侍立在旁,杨先生和一些香客也站在附近观望。只见王道士嘴里念念有词地一阵祷告后,点燃一沓黄表,举在空中轻轻地摇晃,待到青烟袅袅升空,白灰飘飘落地,他还毕恭毕敬地跪在那里祈候上天训示,期盼着佛祖、道君为他指点迷津。
沉寂片刻,忽然平地风起,供桌上的那对蜡烛随风闪烁了一阵后熄了一支。王道士痴痴地望着、望着,突然大声惊呼:“啊!显灵了、显灵了!”
三青又惊又喜,急不可待地问:“师父,可以动土了吗?”
“不行!”
“那显的是什么灵?”三青嘟囔起来。
“两支蜡烛熄了一支……”王道士刚露了点口风,回首见附近有人,又把话咽了回去,对三青做了个诡秘的表情,小声地回答:“时辰未到,天机不可泄露!”
三青被不可得知的“天机”蒙在鼓里,但又不敢找师父多问。他心里窝着火、憋着劲,吃罢晚饭便早早地躺在炕上抱头大睡,直睡到半夜才被师父叫醒:“三青、韩禄,快起来、快起来!”
“干啥呀?师父。”三青勉强坐起,但仍是睡眼惺忪。
“时辰到了!”
韩禄一听,翻身便起:“去开洞吗?”
“开洞。”
三青听说开洞,睡意全消,一面披衣一面仍禁不住地追问:“师父,可以泄露天机了吗?”
王道士故弄玄虚,轻声细语地透露了他悟出的玄机:“平地起风是天神传话,吹熄蜡烛是黑夜,烛熄一支是夜半。这说明佛祖、道君准我们动土开洞,时辰是烛熄月黑天,三更半夜时!”
趁着夜深人静,三青、韩禄扛着工具跟随王道士进入 16 窟。在烛光照亮的甬道里,当韩禄舞动铁锨铲掉北墙右下方绘有壁画的抹灰墙壁后,现出了一堵用土坯砌成的墙体,渐次撤去土坯,一道结实的木门便呈现在眼前。韩禄见状,上前一步伸手要去开门,又被手举蜡烛的王道士阻止:“等等,等等!”
“还等什么?”汗流浃背的韩禄不解地问。
“你没见,这门还没开,风都来了!”
“有风多好呀,我正嫌热哩!”
“可这真要是黑风洞,一开门不怕风把我们吸到东海去?”
“我会水,不怕。你们往后退,我来开门。”
“你不怕,我怕。要不找根绳子把你拴上吧!”
“师父,别担心,就让我跟韩大哥先进去,等找到了上天的路,再回来接你。”站立在土坯上的三青边说边往前移,没料到脚下踏虚一步,无意中前窜的身子既撞上王道士,又撞上了紧靠在木门前的韩禄。毫无防备的韩禄受撞,上身向前一扑,不偏不倚刚好把那不知封了多少年的木门撞开;而王道士被撞后,身子晃了晃,手里的蜡烛晃熄了,霎时间,洞窟里一片漆黑。
此时,洞窟外已近黎明。树丛中,除了影绰可见少数露宿的香客和马匹外,在距离16窟不远处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正密切注视着 16 窟的动静。
洞里的蜡烛又点燃了。光亮所及,但见那木门之后既见不到上天入地的通道,也不像佛祖、道君的殿堂,而是个贮满了经卷、布袋的暗窟。那堆积如山的一袋袋、一捆捆经卷、文书,从地面直堆到窟顶,从门后直堆到窟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把窟壁遮掩得严严实实,只在中间留下一条又狭又窄的通道。
韩禄面对满眼的经卷、文书,禁不住地惊叹:“啊!谁把这么多书藏在这儿?”
看得眼花缭乱的三青也惊奇不已:“师父,藏这么多书在这儿干啥?”
“是呀!谁藏的?藏在这儿干啥?”看得瞠目结舌的王道士也是无话可答,稍稍思索了一会儿,才勉强地猜测道:“凡人哪能有这么多书,早年我曾听静海法师说唐僧法师去西天取经时,见如来佛有经三藏,一藏谈天,一藏说地,一藏度鬼,共计三十五部,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都存在宝阁之中,这里会不会是佛祖的一个藏经洞?”
就这样,藏经洞被打开了,按王道士的记载时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五更时分。等忙碌了一夜的师徒仨从 16 窟出来时已经快天明了,又困又累的他们因为还要去为杨先生另行安排一个抄经的地方,匆忙间只是找来一些旧木椽、木板,简单地遮挡了一下那道门框早已破损的洞门而未能将洞口严密封好。没想到仓促间的这一疏忽,竟留下后患。就在他们离去不久,那里随即遭遇不测。